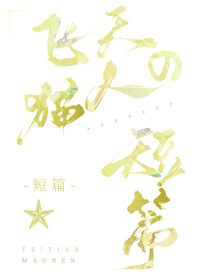入京
啓程入京的日期來得很快,晃眼間,半個月的奔波勞累,許鹿竹的心情沒有因為沿途風景變得很好,反而平靜得如一灘死水,風波并未吹起水浪。
一切都變了,因為離開了桃幽縣,因為一入京城,便知以往皆為過往。
從此再無羽涅,那個新認識的朋友,相處不過一年,便永存記憶。
而她們身邊,俨然多了一個遙不可及,隔着一層無形障礙的身份。
靖王殿下—趙景澤。
三人在入京城前兵分兩路,靖王殿下早已經為州南栀安排好了住所。
很貼心的,隔着一道牆,隔壁鄰居就是陳緣。
将她放在陳緣身邊或許于她而言是一種心靈上的安慰,至少在京城不是孜然一身,他也确定,陳緣會一定程度上照顧着她。
至于許鹿竹,則是跟着他入了靖王府。
生活忽而轉變,急速得根本未有時間适應,京城處處是眼睛,稍有不慎,一切都化為虛無,甚至于萬劫不複。
州南栀只一把劍,腰間一鞭子,推開了這檀香木制成的輝煌大門。
院內,一墨白色衣裳的男子緩緩回過頭,手上一把随之打開的折扇。
面帶微笑,那雙眼總是溫柔似水,氣質如竹蘭,雅淡而舒心。
“總算等到你來了。”
陳緣也只是先一步回到了京城,整個人卻是消瘦了一些,不知是書生自帶的秀氣柔弱還是因為本就偏瘦挺拔的身子,此時在州南栀眼中更像一棵不偏不倚的竹子了。
也就州南栀一人,陳緣溫柔說道,“路上奔波肯定勞累了,飯菜都已經準備好了。南栀,從此以後我們就是鄰居了。”
“屋內的家具一切備置妥當,我比你們先回一步,靖王殿下也吩咐了下人,将屋子給打掃幹淨,每天都開窗透風,就是為了讓那油漆味給散出去。”他跟在州南栀旁邊,不徐不緩。
淡定自若的表現很好的将心中的郁悶給掩蓋,他沒有想到羽涅竟然是靖王殿下。
她擡眼,語氣稀松平常,“你不回陳府住?”
他啞然一笑,甚是不在乎,“回去也是融不進去,不必了。我一個人住,倒顯得自在許多。”
他的身世州南栀在認識不久,就知道一些,但從未過問。
州南栀進屋,有沒有什麽行李需要放置,諾大的房子,只她一人居住,倒是有些不習慣。
桌面上擺滿的飯菜還冒着些許熱氣。
瞧着她面色不佳,陳緣将一張凳子拉開,知道是一路上的奔波将人給累麻木了,“有公務在身,不能親自幫你搬行李來京城,你離開後,我就讓人去你家中取一些行李,這會子應該在路上。”
“謝謝!”州南栀語氣雖是冷冷的,但臉上的表情是極其放松的。
“明日就可去大理寺了,我同你一起。”
州南栀默了一秒,“不必了,你有你的公務,來時師父都囑咐我了。”
“那便好。”
“大理寺的工作很忙?”州南栀輕聲詢問,“你都瘦了些。”
“不忙,是衣服顯瘦。”
院子裏還養了一條小狗,忽然從裏面跑出來,自然的蹭到陳緣的腳邊,輕吐舌頭,“你一個人住在府中,我不放心,便自作主張給你養了一條小狗。”
陳緣将小狗抱起,沒逗兩下,那小狗雙腿狠狠一瞪,撲進了州南栀懷中,在陳緣墨白色的絲綢布料上留下淺顯的痕跡。
州南栀将小狗抱在腿上,逗弄着,歪着頭看它,時而又點點它的鼻子,又碰碰它的眼睫毛,玩得不亦樂乎。
飯桌上的菜冒着熱氣,然而筷子還未能動,州南栀道,“等一下靖王殿下和鹿竹,他們一會便過來了。”
陳緣輕笑,“靖王府上的菜品可比我準備的好吃多了,想吃什麽沒有呀?如今久久未來,我們還要等嘛?”
陳緣緊盯着她臉上的神情,這方試探,倒是丢了他平日裏的禮儀,并未像是他能說的話語。
“可能是被其他事情給絆住了吧!”州南栀摟着小狗,順着它的毛,她只是想等着許鹿竹。
陳緣換了姿勢,正襟危坐,看向州南栀,再次開口,“南栀,若是餓了,我們就先吃吧!”
“還是再等等吧,這屋子是他準備的,若是第一頓飯不等他一起吃,總歸是不好的。”
陳緣點頭,他很想詢問州南栀等的是靖王殿下還是許鹿竹,一番話到了口中因為自尊堵在了喉嚨裏。小狗被州南栀逗得開心了,“要是爺爺在這,肯定要說這屋子裏沒有一個人懂理了。”
“嗯。便在等一等。”
又等了幾分鐘,桌上飯菜冒氣的高度又降了。
小狗忽而掙脫她的懷抱,跑向了院子中。
是靖王殿下和許鹿竹。
在這府中,不用行禮。
但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羽涅了,有的只是靖王殿下趙景澤。
陳緣沒有敘舊,吃過飯後還有公務在身,便去大理寺了,諾大的屋內只剩下兩人。
“當年謀反事件,餘丞相以一己之力,保下了兩名皇子。”靖王殿下打開了話茬子。
那兩位皇子便是靖王和豫王,而辰王卻是永遠停留在了十二歲,餘丞相以生命之軀立下汗馬功勞。
作為天妒英才,最有望繼承皇位的便是皇後所出的辰王,他更是官家給予的重任,大臣心目中未來的帝王,文武皆有傑出大臣指導,若是活下來的其中一個是辰王,現如今,就不會出現兩庭紛争的局面。
許鹿竹知道餘丞相,曾經在朝廷中是丞相之首,而如今的丞相之首是柳丞相柳纮氿。
“造成那日的慘案,當年是一封傳信,逼迫餘丞相殺死兩位皇子,而那封信,”靖王殿下沉默了。
許鹿竹平靜的回,“這封信,說是許家傳來的。”
官家一共有三位皇子,年紀皆相仿,州南栀眼皮輕擡,“那當年的豫王殿下不在嘛?”
趙景澤抿了口茶,杯子遮住了眼,語氣平淡沉穩,“巧合,也因為這巧合,沒有讓他卷入這起大事,那天,豫王殿下生病了,只有我和皇弟兩人被父親召集入宮。”
真是巧合?許鹿竹眼眸下垂,所有的事情猶如在一張蜘蛛網上被纏住,牽一發則動全網,掙紮不出個所以然。
靖王殿下視線聚集于許鹿竹,盯着她的神情道,“但如今,有一個突破口,便是郎溪将軍。”他說這話時,又看向了州南栀。
州南栀臉上沒有一絲情緒,緩緩開口,“這郎溪将軍,當年不是戰死沙場了嘛?”
趙景澤眼眸一閃,她說的确實對,郎溪将軍戰死沙場,是對外的說法。
郎溪将軍,戰場上無敵手,自他鎮守邊疆,外無敵兇來犯。
趙景策:“對,在百姓心中是戰死沙場了,但那封信,就是他的侍衛幫許家送出的。”
此話一出,州南栀忙問道,“郎溪将軍難道還活着?”
趙景策微微揚起下巴,“可能,郎溪将軍并未死亡,我也一直在暗中尋找此人的下落。”
許鹿竹知道了,羽涅這話的意思,就是找到郎溪将軍,極有可能證實許州兩家的清白。
大理寺。
州南栀站在外面特意看了幾眼,與師父描述的區別很大,長嘆一聲,今日出門前明明特意看了日歷,大吉。
将師父寫的推薦信遞給大理寺少卿張冼大人,州南栀恭恭敬敬站在面前,低頭一言不發。
張冼大人端坐于椅子上,手扶着額頭,一身紅色官服,襯得整個人溫文爾雅,一股儒雅書生之氣,兩鬓的白發更添沉穩。
他将信放下,音色低沉,眉梢帶笑,眼神帶着寵溺看向她,“東西都拿來了?他就篤定我一定會給他這個面子。”
州南栀茫然,明明是含笑的語言,卻是帶着一股陰陽的語氣。
“你是他徒弟?”
州南栀點頭。
“你可知,你師父從前就是在這大理寺混的?”
這她不知,謙卑回應,“師父同我說他并未在大理寺任職過。”
對面人呵了一聲,幽幽說道,一字一句口齒清晰,緩緩落入她耳中,“我們倆當時喜歡上同一個姑娘,結果,你看到了,他跑去一個小地方療傷了。”
州南栀在心中默默深吸一口氣,所以師父會覺得他一定會讓自己進大理寺?
不知不覺挖到師父的往事,州南栀仍舊神情淡然,眉眼間是擺脫世間俗事的豁達之意。
“你是大理寺第二個入職的女孩,就和劉鋪快一同到劉裴玄劉少卿那裏做事吧!”
州南栀覺得第一天入職大理寺的日子,按道理确實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。
她還在想如何與新同事相處,然而她一去到大理寺,卻根本就不用想這問題。
人人都很匆忙,做着自己手頭上的事情,與她擦身而過,根本就未搭理她。
甚至于去劉少卿那裏報道,也受到了冷落對待。
劉少卿不同于張少卿,坐姿端正,在批改着案折。
不曾擡眼,一話都未給她。
州南栀也站定于前,沒有他的安排,自己在這也不知幹些什麽事。
又站定了一會兒,他擡起眼皮,眼神中掠過一絲驚訝,随之就是不屑的眼神打量着她。
這就是張少卿說要送給自己的助手?
他這才拿起她的資料簡單看了兩眼,手按着太陽穴,擡眼看着她,“州南栀,曾經也是個鋪快?也是像如今一樣是靠關系戶進去的嘛?”
州南栀臉上神情平靜,輕聲回,“不是。”
“行,姑且相信你不是,也破了幾起案子,但你知道我們這大理寺是很難進的吧!你這不用考試就被推薦了,我這人挺看不起關系戶的。”
她站姿始終規恭恭敬敬,“劉少卿想要說些什麽?”
他唇角嘲諷上揚,滿臉不屑一顧,“張少卿是安排你做我的助手的,接受嘛?州鋪頭。”
他在喚州鋪頭時重重的念了聲,言語裏都是嘲諷。
州南栀顯然不在乎,啓唇,“需要做些什麽?”
“把這些去年的案卷給整理好,旁邊那個空位看到了嗎,以後就是你的辦公地了。”
“是。”沒有一絲怨氣,她将這些案卷拿到了旁邊的桌面上,桌面上整理得跟幹淨,她将劍放在了旁邊,開始整理案卷。
她好像又回到了當初在桃幽縣剛進衙門時,被瞧不起,但師父給她撐腰。
如今在這,她孤身一人。
過了一會兒,周曹安靜,劉少卿眼神從案卷中移起,眼神略過州南栀,那女子太過于安靜,倒讓他忘了她的存在,伏筆認真,他唇角微微上揚,“州姑娘,你一介女流之輩,早已經到了婚假年齡,怎麽不嫁人,反而跑到了這大理寺,這恐怕不是你待的地方。”
她循聲望去,接着起身,眼神恭恭敬敬,語氣稀松平常,“我喜歡辦案。”
他輕聲哼了一聲,自家小妹也是如此,如今大理寺只有兩個女生,偏生兩個都是關系戶。
然而相處下來,州南栀很冷,都是劉少卿問一句她便答一句,其餘之外是話語她都不曾說過一句,始終低頭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,有不會的便過來請教。
安靜,又勤奮。
“你只身一人來到大理寺,家中長輩也是願意?”
“我父母早已經去世,身邊的朋友都很支持。”她又是平靜的語氣,就只是在敘述一件平常的事情。
劉少卿在她臉上看不到任何其它神情。
“對不起,但州姑娘,我不喜歡也不認同女子在這辦案。”
“哦。”她回。還是不知他想要表達些什麽。
“所以我會想盡辦法讓你離開。”
刁難嗎?她以前在衙門所受的痛苦又來了。
眼神劃過劉少卿,州南栀只是輕輕點頭,對這些話語明顯不在乎,不感興趣。
這孤傲一世的神情讓劉裴玄更感興趣了。
她的關系戶是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