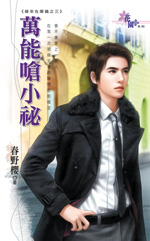大約一炷香後。
“我去趟茅房!”
許幻竹終于推開面前的三個空盤子, ‘嗖’地起身離開。
生怕他們還要再給她剝什麽,跑得那叫一個腳步利落。
許幻竹才起身離開,淩清虛也站起來, 他走到時霁身後,一只手搭在他肩上, “少君,我也去透透氣, 你留下陪着裴姑娘, 我一會兒便回來。”
說完, 也不等時霁回話, 提步就追上了許幻竹,往外邊去了。
裴照煙擡頭看了時霁一眼, 他此時正皺着眉頭, 十分嫌棄地拍着肩膀上方才被淩清虛碰過的地方。
淩清虛好賴比他要大一百來歲了, 玩得還不是他剩下的, 學人精!
他鄙夷地看向淩清虛離開的背影, 又慢慢收回視線, 反正淩清虛追上去也沒用,随他去折騰。
“少君,你若也想出去便自管去吧, 我可以一個人在這裏等你們。”
君沉碧此時不知自己的身份早已被看穿,還十分盡職盡責地扮演着裴照雪姐姐的角色。
“我不想出去”,時霁一口回絕,“正好又事想要問問裴姑娘。”
“少君請問。”
“小雪今日與我不太親近,反倒與柳公子聊得頗為開懷。你是她的姐姐, 可知這是為何?”時霁倒是不認為君沉碧能答出什麽來,畢竟與他這個假未婚夫比起來, 她這個假姐姐也好不到哪裏去。許幻竹大概也不會同她說什麽。
只是閑着也是閑着,便就問問吧。
他心裏雖這麽想着,但看向君沉碧的眼神,還是藏了些期待。
君沉碧摸了摸眼前的果盤,将落在桌面上的葡萄皮撿起放進了盤子裏,猶豫了幾息才開口:“妹妹她……”
時霁接着問:“她怎麽了?”
“她說,少君追得太緊了,她有些煩。”君沉碧說完這一句,不敢去看時霁的表情,又補充了句:“少君勿怪,妹妹心直口快,大概不是這個意思。”
他追得太緊了?
有些煩?
別告訴他她就是單純喜歡淩清虛那般端着的。
“我不怪她”,時霁黑着臉站起,“我也去院裏透透氣。”
接着便長腿一邁,往外走了。
許幻竹上完茅房并未馬上回去,而是停在百悅樓後院的一處小角落裏,朝着天上輕聲吹了道口哨。
伴着她那道口哨聲,一只小麻雀從屋檐上飛下,落在她肩上。
這就是她的專屬傳信小麻雀,她從裴家醒來時,這麻雀便跟在身邊,小東西看着雖呆了些,但也湊合能用。
她輕輕點着麻雀的腦袋,“今日在雲溪的亭子裏,他們兩人說了什麽?”
許幻竹腳下随意踢着石子兒,眼睛看向她從酒樓裏出來的過道口,她是從後門出來的,這條道還是時霁帶着她走的。
小麻雀攀着她的肩膀朝裏走了幾步,靠在她耳朵邊,叽叽喳喳了半晌。
許幻竹認真地聽着,她眉間忽地一挑,她猜得沒錯,那人果然時霁。搞了半天,加上她們師徒倆,誤入這玲珑塔的居然有四個人。
許幻竹正想着,一會進去了要不要直接攤牌商量出去的法子。
畢竟認真說起來,她是真的不想攻略淩清虛啊。
“裴姑娘。”有人叫她。
許幻竹看向來人,是百悅樓中的那個喜鵲姑娘,
她提着個水壺,來後院澆花。
許幻竹這才注意到自己身後的牆角下,種了一片月見草。
她給喜鵲讓出一條路來,“喜鵲姑娘,這花是你種的?”
“是的”,喜鵲往花叢裏澆着水,繼續道:“少君也喜歡這些花草,閑着無事,我便種了一些,這樣他來樓裏時見了,心情也能好一些。”
許幻竹蹲下輕輕摸了摸粉色的花苞,她忽然想起什麽似的,擡頭問喜鵲:“那姑娘可知道,月見草的花語是什麽?”
院落中掃過一陣清風,清風掠過牆角的一叢花,拂開許幻竹額前的碎發。許幻竹看見喜鵲停下動作,她一手托着水壺,另一只手彎腰折下一支月見草,遞到許幻竹手裏。
許幻竹伸手接過,便聽見喜鵲接着開口:“月見草,又名待宵草,一次播種,開花不絕”,許幻竹将花朵輕放在鼻尖上,癢癢的,頭頂又傳來喜鵲的聲音,“月見草的花語便是,默默的愛。”
街道上有人放煙花,就在這時候,一朵彩色的煙花綻放在百悅樓的天幕上,巨大的轟鳴聲響環繞在耳邊。
一聲又一聲。
“你栽的那花還挺好看的。”
“那師尊可知它們有什麽寓意?”
許幻竹顧不得擡頭去欣賞漫天繁華,只靜靜地盯着手裏的粉色花朵。
“默默的……愛。”她忽然覺得手裏這花,無端有些灼熱燙手。
煙花漸漸停了,喜鵲也不知什麽時候已經離開了。許幻竹揉了揉發麻的腿,正準備站起來,頭頂忽然罩下一個陰影。
她還來不及擡頭,那人忽地将她撲倒,天旋地轉間,耳邊傳來一句:“小心!”
許幻竹猛地睜大雙眼,只見上空忽地蹿出來一道黑影。
那黑影,她不可謂不熟悉。
影子動作十分快,起初是朝着許幻竹的方向沖過來的,後來淩清虛将她撲倒後,那黑影便直沖沖地朝着淩清虛了。
許幻竹也不知哪來的力氣,扣着淩清虛的肩膀猛地從地上翻身而起……
時霁到後院之時,見到的便是這麽一副場景。
一只長着牛頭馬面猴身的怪物從樹上一躍而下,朝着淩清虛生生撲過來。而在那怪物要張嘴咬上淩清虛的下一瞬,許幻竹從地上一躍而起,将他擋在身後,于是這兩道獠牙便破進了她的脖頸。
“裴照雪!”
“裴姑娘!”
時霁和淩清虛飛身上前,兩人一左一右圈在那怪物兩側。時霁蓄力往它身上砸下一道白羽飛箭,淩清虛吸起地面上的沙塊石礫聚成一道網朝它打來。只是那東西身手敏捷又皮糙肉厚,實在是不好對付。
君沉碧聽見打鬥的聲音趕過來時,不知發生了什麽事,她正要上前去幫忙,時霁沖她喊道:“快帶她回去!”
分神間,時霁被拿東西的爪子抓了一把,右肩的衣裳破了個洞。
“你怎麽樣了?”許幻竹被君沉碧攬着往外走,她捂着脖子,不知是流了血的緣故還是怎的,只覺得腦袋昏昏沉沉的,也沒力氣答話,便幹脆就讓君沉碧拖着走。
百悅樓裏一片混亂。
兩人出了百悅樓大門正要往裴家趕,有人忽然攔在她們倆跟前。
君沉碧擡頭,只見那女子一襲彩衣,身後跟着宮城中巡邏的白羽衛。
她正要開口求救,卻見那人出聲喝道:“裴照雪被妖物咬傷,這妖毒霸道蠻橫,恐怕會傳播,為了城中百姓的安全,請諸位快将這兩人捉了送去宮裏處置。”
于是君沉碧和許幻竹被團團圍住,那一群白羽衛個個嚴肅平整,不容她們多說半句便押着她們去了宮裏。
許幻竹開始有意識時,發現自己已經被關進了地牢裏。
牢裏陰冷潮濕,透着股死老鼠味兒。
她擡手摸向自己脖間的傷口,只摸到一塊白布,應是被人包好了。
許幻竹走到牢房的門邊,搖了搖牢門上的鎖鏈,一個穿着黑衣的牢頭走到她跟前不耐煩道:“幹什麽?”
“為什麽把我關進來?”
那牢頭看了一眼許幻竹,不屑道:“還以為自己是少君的未婚妻呢?你如今中了妖毒,不将你關起來,難道留在外頭害我們不成?”
許幻竹又摸了摸脖子,這不是妖毒。今日那怪物的模樣,她見過的,與十年前漁陽村子裏襲來的那群魔潮一樣。她之前就被魔潮咬過,傷好之後并沒有什麽事。怎麽聽着人的意思,這毒好像還會傳染似的。
“我不會害你們,大哥能不能替我跟郡王說說,将我放出去?”許幻竹兩只手抓在牢門上,但又立刻被彈了回來。
“你離這出口遠些,這可是青泸郡中特意用來關人的地方,你碰一下都要皮開肉綻的。實話和你說了吧,咬你的那妖物還咬了百悅樓中的一個夥計,那夥計比你傷得厲害些,已經長出了獠牙和長甲,變成妖物了!”
“依我看吶,你的下場估計也差不多。郡王看在你之前救過少君的份上,還叫我們好好關照你,你可消停地在裏頭呆着吧。”
“那白月晏呢?”許幻竹手心裂開幾道傷痕,有血絲一點點地往外冒,她不敢再碰那牢門,遠遠站着問他。
“少君和白羽衛還在捉那只妖物……诶剛叫你消停呆着,你問這些有什麽用呢?郡王連夜取消了你和少君的婚事,少君便是回來了,也不會來救你的。”
許幻竹聞言默默退回了角落,蹲在了地上。
那牢頭見她不再折騰,便也離開了。
牙有些癢。
許幻竹伸手摸了摸,嘴角的兩顆牙齒好像變得長了,尖了。
不是吧。
她怎麽這麽倒黴?
無緣無故被拉到這玲珑塔中出不去也就算了,裴照雪這身體讓她喝不了酒,睡不了好覺也就算了,如今還被這不知是哪冒出來的魔潮咬了一口,随時還有魔變的可能。
越想越氣,許幻竹捏緊了拳頭又痛得立馬松開。
腦子裏那股眩暈感又襲來,于是她只能靠在牢壁上,慢慢睡了過去。
再一次睜眼時,她是被人掐着臉弄醒的。
耳邊傳來那牢頭的聲音,“少君,你別這樣,我不好交待啊。”
時霁頭也不回,“誰若有什麽意見,讓他來找我。”
“少君?”許幻竹睜開眼,便見時霁面無表情地蹲在她跟前,一只手捏着她的臉,十分粗暴地把她掐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