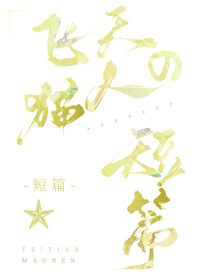佳畫藏美人
院外安靜異常。
州南栀将劍放在桌面上,靜靜的坐在石凳上。眼前熬煮的草藥已經沒有冒出熱氣,最後一點炭火也快要熄滅了。
羽涅給她端來了一杯茶,“想什麽呢?那麽入迷。”
“律法的設立,不是為了規範嗎?是用來維護自己,保護自己的工具,那為什麽,卻變成了制裁受害人的工具。”她說這話時,如鲠在喉,輕輕一句話,猶如一塊大石頭激起千層浪。
羽涅陪在州南栀身邊,他輕輕開口,“辦過的案件太多,受害者之所以選擇了自己拿起武器,以卵擊石,自傷八百的報仇,是因為律法的不完整,是因為律法很多時候是為權勢而所用。”
州南栀喃喃自語,“為權勢所用,呵,呵呵。”
她輕易不落淚,可這一次,她伸手摸了摸臉,掌心那濕熱的淚水,感覺不在是透明色的了,而是血紅色的。
這些淚水,更多就是受害者的淚,進而轉換成血痕,再轉化成家人臉上的淚水。
擡眼間,那個安安靜靜的小木屋內,在下一秒,傳來了大聲哭泣的聲音。
楣莺解脫了。
州南栀轉過身,将那些畫丢在一地,将墨水潑了上去,墨水将畫給染黑,看不到一點畫像的內容,五顏六色在頃刻間黯然失色,這些不該留下的東西,州南栀一把火都給燒了。
羽涅道,“會越來越好的,這件事,知州大人也能看出其背後的意義。”
“那要很久吧,這些可都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。高高的上位者,誰會在乎一個妓女的生命。”
“生命從來就不是平等的。”羽涅回。
州南栀回頭,“你也認為是這樣的嗎?”
“不是我認為不認為,而是就算宣揚了人人平等,可體現在生活中,依然就不是平等的。更何況,如今看來,這句話就是個笑話,不論官家如何說,你若是同你師父說這句話,對他而言也是放屁。”
“所以,天子犯法,與庶民同罪,是假的。”州南栀的斷定太過于絕對。
羽涅這次不說話了,靜靜的站在她的身邊,望着她的側臉,若有所思。
在州南栀即将離開時,羽涅的聲音從後面傳來。
“存在一定的公平,但從未也不可能有絕對公平。”
将卷宗整理後交由縣令大人,州南栀便出了衙門。
見師父莫求整個人眉開眼笑,“南栀乖徒,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,連知州大人都在忍不住贊嘆你,雖是女兒身,但膽量謀略不輸男兒。”
州南栀點頭,對他說的話,知州大人的贊美無任何心情,“那師父,麻煩日後替我謝過知州大人,他穆贊了。”
莫求摸了摸下巴粗犷的胡子,“南栀乖徒兒,要不你幫我問問,你那個戴面具的朋友,願不願意來我們這,加入我們這個為民除害的大家庭呀?”
羽涅的武功高強,自然也是師傅想要求的人才,現在京墨基本上是占着茅坑不怎麽拉屎,又把目光放到了羽涅的身上,找多些人幫他打工,他就能在家悠閑悠閑的喝酒了!
師父真是好計謀!
州南栀臉上揚起淺淺的微笑,語氣卻是有些冷淡,“好,下次我問問。”
莫求是了解自家徒兒,再次叮囑,“那你記得問呀,別忘記了呀!”
楊壽富商一下子失去倆兒子,諾大的財産無人繼承,而州南栀也成了他可怒不可言的人。但證據也證明的确是自己兒子犯了法,那些被換掉的小厮都被找了回來一一審問,他饒是投太多的錢財,也終究是于事無補。
索性,楊壽便将這萬貫家財都給換取了銀兩,自己一個人雲游在外了。
關于楊全的罪證,單是私自售賣五石散一條便讓其沒有了活路,只是他上頭的人,五石散的來源,他只說是不知。
畫蓮不在春醉樓了,而是一個人過着全新的生活。
這件事到此告一段落,生活依舊如往常般。
衙門裏。
州南栀進去的時候,莫求正一腳踩在凳子上,和其他捕快興高采烈的堵着牌。
她淡定的走進去,熟練的拿起桌子上的水杯,仰頭一口悶。
莫求贏了一把,起身湊到州南栀身邊,“南栀乖徒,巡街回來了?”
州南栀抿唇不語,她現在很是生氣,在大街上巡街時被幾個浪蕩子調戲了一番,在莫求那雙大眼睛的注視下,她緩緩開口,“師父,你在賭錢呀?”
莫求;……..
明明一眼就知道的問題還要問,州南栀每次都愛這麽回師父。
“行了,前廳有人在等你。”
“師父,是誰?”
“哼,你的桃花債呗。”他說完,又大搖大擺回到了賭桌上。
州南栀嘆了一口氣,他回來了。
拉開的凳子還沒有坐下,又拿着桌子上的劍往前廳走去了。
循着長廊走去,州南栀心情難以平複,樹上的鳥叫聲讓州南栀心煩不已。
在跨入門坎時,背對着自己站立的陳緣,一身墨白色山水繡衣裳,整個人溫婉獨有的氣質渾然天成。
陳緣身上總是有股與讀書人不一樣的氣味,是渾然天成的,如荷花般出淤泥而不染。
許爺爺曾經就說過,陳緣這股子氣質,即使他不飽讀詩書,照樣可以裝讀書人。
陳緣耳力很好,在州南栀跨過門檻時就知道要等的人來了,那熟悉的腳步聲,他立即轉過身去,輕輕喚了一聲,“南栀。”
此時恰好有微風吹過,将她肩上的碎發吹得散亂。
她止步于兩人相距五米處,“陳公子,不知找我所為何事?”
他臉上笑容未淡,州南栀故作的疏離感并未讓他難過,“坐下說話吧。”
州南栀就近坐在主位下方,陳緣慢慢向她走過去,坐在她的旁邊。
他走路時玉佩發出的聲音與旁邊系着的香囊形成明顯對比,那玉佩晶瑩剔透,是上好的材質煉制而成,而旁邊的香囊,普通的布料搭配上簡簡單單的中藥材,不好看但勝在實用。
州南栀下意識盯着那玉佩和香囊看,擡起眼眸時,目光和他正對上,州南栀迅速移開了視線,撚起桌子上的茶壺給自己倒了一杯茶。
他坐下時,眼神直直看向州南栀,“我去科考的這段日子,你過得還好吧?”
“嗯,日子過得也算是精彩絕倫,陳公子是有什麽事嗎?”她對上他的目光。
眼底下的黑眼圈,兩頰的黑青,胡渣也漸漸冒了一些出來。
按道理,他應該是下下周回來的,但如今卻是提前了許多,一路上的奔波随處可見。
“我接到京墨的信,說你要成婚了,趕着回來,看能不能趕上,還來不來得及。”
他的話語未曾說完,州南栀抿了抿嘴唇,“什麽時候放榜?”
“下個月。”
“那我祝你萬事如意!”州南栀起身。
正快要離去時,陳緣又道,“南栀,那羽涅,可是你的未婚夫?”
州南栀立定,僵直了身子,緩緩吐出,“是。”
随後便離開了。
陳緣懸着的心終于落了地,不僅是落了地,還碎了一片,辛苦了多年的讀書,科舉路上的幸苦都不曾落過淚,這一刻,眼尾竟悄無聲息的冒出了淚光。
許家藥堂。
“南栀,你和羽涅辦婚禮嘛?”京墨将掉落在桌子上的藥材一一拾起。
州南栀眨了眨眼睛,沉聲出口,“不辦。”目光又緊緊鎖住京墨,“我的事情你怎麽那麽感興趣了?還真的是辛苦你通風報信了。”
京墨不好意思的撓了撓頭,“陳緣回來了?”
“嗯。”
簡單的一個字,許鹿竹便明白了,能讓州南栀如此生氣的只有一個人,那就是陳緣。
京墨聳了聳肩膀,“我就覺得羽涅這人甚是神秘,南栀,你跟他走太近,最終吃虧的是你。”
州南栀湊近了他,京墨下意識往後退。
聞此,她挽唇一笑,“都說了只是把這個消息放出去,又不是真的步入婚姻。你若是把這件事也透露給陳緣,你別怨我把許鹿竹從你身邊奪了去。”
許鹿竹還特別配合的摟住了州南栀的肩膀。
京墨垂頭,表示任命。
話畢,羽涅也走了進來,“州姑娘,我沒有什麽意見,至始至終我答應結婚,也不過是想報答救命之恩,況且我和州姑娘本就未情投意合,匆匆步入婚姻,倒是玷污了婚姻這神聖的過程。”
州南栀啓唇,“對不起,是我的問題。”
“無礙,只是我還欠你一條命。”
這番對話又引起了京墨的注意。
“不逗你了,是羽涅說,用婚姻去解決這件事情,對南栀的名聲極為不利。”許鹿竹柔聲解釋。
兩人的婚禮原本是計劃在五日後,現如今因為陳緣快馬加鞭的趕了回來而取消,準備好了一切的州爺爺倒不滿了,将州南栀訓斥個狗血噴頭,連一向被他喜愛的京墨也不能幸免。
他看着這些為婚禮準備的東西,“南栀,你當錢容易賺呀?你說成婚就成婚,說不成婚就不成婚,你都十九了,按道理早就該成婚了,可你非得要踏入公門的路,好,我容你,現在呢?你和陳緣的事情,是越來越不可能了,我們家本來就比不上人家,若是下個月中了舉,就要到京城上任了,你和他,從河的距離,到以後的海的距離。”
京墨捂了捂被州爺爺誤傷的額頭,“怎麽受傷的總是我。”
州爺爺瞥了他一眼,又看向州南栀。
羽涅從外邊進來,手裏邊還拿着一個雞蛋,遞給他敷額頭。
“羽涅,你願不願意娶我家孫女?”
他看了一眼州南栀,“州爺爺,這得過問南栀。”
“我不願意。”州南栀道。
眼見州爺爺臉上的怒火快要把持不住了,京墨拿着雞蛋不停的揉着額頭,“州爺爺,南栀喜歡一切美的事物,你看他,老是戴着個面具,可能面具之下就是個醜惡的嘴臉。”
羽涅喉結微微滑動,“我左眼眼角上的确有個淡淡的,細小的疤痕。”
州爺爺品了品茶,“南栀,門當戶對對于陳緣這種家庭,那是必須的,若是你一年前真的嫁過去了,過得就幸福許多了。”
京墨啧嘆幾聲,揉完了雞蛋,淡定的将蛋殼給掰掉。
州爺爺伸腳輕輕踹了他一腳,“你和我家南栀玩得好,幫我勸一下。”伸手奪過他剛剛掰好的雞蛋,又小聲呢喃了一句,“又浪費我家的雞蛋。”
京墨兩手攤着,撇嘴別開臉,“我不勸。”正是因為和州南栀玩得好,他更知道勸了也沒有用,沒有人能強迫她幹自己不想幹的事情。
聽羽涅說,自他離開之後,州爺爺和州南栀聊了什麽一個晚上,州南栀也并未改變自己的主意。
最後是州爺爺熬不過去了,擺擺手,随她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