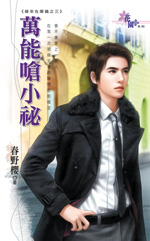孟琨玉,曾經也是修真界名動一時的劍修。
凡是抵達元嬰之境的修士,都會在玉簡書卷上留下一筆記載,即便是散修、魔修突破,都常常被記錄其中,更別提這種正道劍修。
此人勤奮刻苦、天資卓越,曾經一劍斬退三千英才,乘飛劍鋪路大笑而去,被視為一等一的傲氣狂徒。
只是她從剛剛踏入金丹開始,便從清源天女手中接過了清源劍派的實際主導權,以大師姐的身份處理門派內政。那時清源天女乃是化神期老祖,雖然隕落于大道之前,但清源劍派卻正是烈火烹油、鮮花着錦之勢。
清源天女一死,門派地位也一落千丈,客座長老越權幹涉,而她的三個弟子卻都還未突破,實力不足,幾乎所有人都判定這門派的主人即将改名易姓,被盜取千載基業,然而孟琨玉卻以玉清真人的身份接掌,收斂一身鋒芒,出人意料地扛了下來。
她的心機、手段、城府,以及行事作風、判斷思考,絕非一個單純劍修。也正是這樣,原本天才英拔、亮博不群的孟琨玉,也被門派事務拖累了精神,一個年少動天下的天才,竟然拖到壽數将盡、前途無望的地步。
十四年前,她的師妹謝風息渡劫未成,心境受阻,一生的前程幾乎盡毀,而孟琨玉也算出自己時日無多,短則五年,長則二十年,就會徹底油盡燈枯。
孟琨玉與謝風息徹夜長談,燈燭亮了整夜,在燭淚成灰,日光映過枯蠟的第二日,孟琨玉将清源劍派的掌教之位傳給了小師妹沉萱。
故而,沉萱除了玉真劍君之名以外,還身為清源劍派的掌教,手持一把天寶玄器昆吾劍,因為昆吾劍為玄器,幾乎只有化神期的老祖們才持有,故而她也有幸被尊為昆吾劍仙。
十四年前的那件事,孟琨玉也曾懷疑過,只不過她更為信任自己朝夕相處的小師妹,認為她不會做出如此斷情絕義之事,便真的以為是明二公子尋到了元配真愛,師妹另娶他人,是無可奈何之舉。
然而今日,那個在沉萱口中留書私奔的二公子,卻活生生地站在眼前,指責謝風息與沉萱狼狽為奸、擄走圈禁他,這實在太挑戰孟琨玉的底線了。
她身軀只有六歲左右,臉頰圓潤,但此刻面沉如水,緊皺眉頭,她穿過清源劍派巨大的萬劍冢,在遍地插滿名品飛劍的蒼莽廣場上行過,周遭的內門弟子見到她,無不躬身行禮,口稱劍君。
明無塵跟随着她,但此刻已經将鬥笠長紗撥下來,隐藏存在感。所以劍修們大多見到的是梅問情與賀離恨兩人,這兩人生得實在醒目,俊美者鋒銳,清豔者溫潤,實在是少見的既矛盾、又般配。
四周劍修有男有女,只不過女修要多些,大概占到六成。若是在主攻醫毒的門派或是合歡宗,這個比例則會大大變化,合歡宗的男弟子更是要占到七成以上。
在劍修弟子的一路行禮之下,孟琨玉很快便将幾人帶到清源劍派的內殿,雖是內殿,但也寬闊廣大,中間拿來鬥法恐怕都足夠。
孟琨玉進了內殿,見上首無人,拽了一下守殿弟子的袖子,怒氣沖沖:“沉萱人在哪兒?謝風息呢?叫她們兩個給本座滾出來。”
若不是認識這是本門劍君,這弟子簡直要以為是什麽邪魔外道來搗亂了,她從沒見過孟元君發這麽大的火,哆嗦了一下,連忙道:“掌門去了無極宗,說是午後歸來,二長老的行蹤,向來神出鬼沒,晚輩何曾知曉啊。”
這個二長老跟客座長老的含金量可不一樣,乃是清源劍派的嫡系,可以共參大事,地位崇高。
孟琨玉道:“去敲鐘,給我把人叫回來。”
那守殿弟子瞪大眼眸:“敲鐘?請您三思,沒有非死即傷的大事,門派內是不能敲鐘的啊!上一次鐘鳴,還是祖師離世……”
“讓你去你就去。”孟琨玉怒道,“我要讓這兩個孽障給活活氣死了,難道我死不能敲鐘?還是我這師姐做得不好,這千秋基業傳給她,我倒成了罪人了!”
守殿弟子再不敢言,連忙轉身離去,拿着孟琨玉的令牌前往吩咐。大約半燭香後,清源劍派山門頂上的巨大古鐘,響起了一聲幾乎震蕩寰宇的悠長鳴響。
一、二、三……總共敲了七聲,意思是“十萬火急,速歸。”
在鐘鳴震蕩天下,傳遍整個清虛之境時,一道銳利劍光也突破雲霄,飛快地雲端降下,再掃蕩成一片波光,沖進殿中。
這個叫法确實行之有效。這道劍光一閃,便有渾身鋒芒畢露的身影立在殿內,正是玉真劍君沉萱。
她花顏烏鬓,臉龐雖然極美豔,可望之又極清冷,有一股疏離寒意。發絲之間戴着金梳玉簪,斜斜地綴着一條水晶步搖,雖然無甚表情,但的确如松如柏、凜若秋霜,怪不得一個女子,能讓無極真君那樣的男人為她甘心付出。
若不是她眼中閃過幾許惶急之色,恐怕都看不出是赴鐘鳴而來。
沉萱先是端詳孟琨玉,見師姐雖然面有怒色,卻并無異樣,便收劍向下,合手道:“沉萱見過師姐。”
孟琨玉吐了口氣,試圖冷靜:“謝風息呢?她怎麽不來?”
沉萱道:“師妹不知。”
她不知道,梅問情倒是知道幾分,謝風息被她斷了一臂,元氣大傷,又遠在清虛之境以外,就算是用比飛行法器快的遁光前來,也沒有那麽快,估計三五日之內,甚至她的傷更重些,半個月都未必能到。
“你不知道?你要是不知道,怎麽會跟謝風息幹出這種無恩無義,不知廉恥的事!”
孟琨玉忍不住喝罵她一句,招手讓明無塵過來,兩人當面對質。
時隔十餘年,明無塵再度見她,此人已從一個身懷抱負的金丹真人,成為了人人尊敬的昆吾劍仙,他心中百感交集,不知道是怨恨還是嘆息,原來年幼相識的青梅竹馬,數百年交情,也有如此涼薄的一日。
“二公子,你不要怕。”孟琨玉道,“有何冤屈,可以直言不諱。”
明無塵深吸了一口氣,将長紗撩了上去。
他已非昔日少年,不再有一身溫潤君子之風,也不再青澀天真,此刻的明二郎,早就在謝風息手裏被養成了豔麗尤物,就算素衣白衫,也透露出一股楚楚動人的風情,他的豹尾藏在衣服底下,可展露出來的這些,已經跟當年判若兩人。
沉萱的眼眸瞳孔緊縮,眼珠幾乎跟着顫了一瞬。
明無塵道:“萱娘……不,劍仙閣下,可還識得二郎?”
沉萱單手支在劍柄上,劍鋒狠狠地嵌入地面,昆吾劍吹毛斷發的鋒芒斬裂了內殿的磚石。她道:“許久不見。”
“昔日我失蹤,劍仙對師姐、對明家,都說的是我跟他人私奔了麽?”明無塵問,“你就沒有,找過我嗎?”
沉萱緩緩地閉上眼,然後又掀起眼睫,神情複雜,一言難盡:“難道二師姐不曾好好待你?”
這話便是承認了。
別說孟琨玉被氣得一口氣差點上不來,連梅問情都跟着琢磨了半天,跟賀郎道:“她這脾氣很硬啊,連迂回都不肯,這樣果斷的心性,只可惜人太無情了。”
賀離恨:“你要是這樣,我就先一步殺回去,捆住你的手,将謝風息那瘋女人的手段在你身上用一遍,看你還敢不敢始亂終棄。”
“咳。”梅問情道,“那哪兒能啊?我多忠貞,是吧小惠。”
小惠姑娘目不斜視,臉上寫着“我只是個紙人,不懂你們之間的情調。”
沉萱這話不僅将孟琨玉氣得夠嗆,連忍耐至此的明無塵都突然控制不住,手指攥得緊緊的,眼角泛紅,咬緊牙根才說出話來:“你知道,好,你把我讓給她了是嗎?可我不曾是個物件,不曾是個禮物,你們憑什麽這麽讓來讓去!”
他快走幾步,逼近沉萱面前,伸手揪住她的領子,當面問道:“你為什麽要說我另結新歡,污蔑我的聲名,你跟你的好師姐根本就是沆瀣一氣、蛇鼠一窩,沒有一個是好東西!沉萱,你告訴我,我哪裏負了你,竟然變成你們師姐妹之間交易的籌碼?你把我送給她換來了什麽?啊?”
沉萱垂眸不答,只是道:“她說會好好待你的。”
明無塵怒不可遏,幾乎從憤怒演變成一股可悲,莫大的哀痛和懊悔侵襲而來,讓他心口悶痛,喘不過氣,揪住她衣領的手漸漸脫力,卻又不甘心,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。
沉萱受了這一巴掌,清冷臉龐上浮出指痕,她既沒有阻攔,也沒有躲。她凝視着明無塵,昔日的二公子被作踐得體無完膚,這種恥辱之中,也有她的過失。
沉萱道:“我是昆吾的執掌人,清源劍派的掌教,我不能犯錯。”
“所以,就只能是我的錯?就只能是我另結新歡,與人私奔,背上罵名?”
明無塵的聲音有點嘶啞,無力地松開手,不停深深呼吸,恢複理智。
“謝師姐她,沒有遵守給我的諾言。”沉萱道,“她說終生只娶你一個,絕不再娶,待你如正君,生前建立共廟,死後合為一墳。”
明無塵閉上眼,苦笑了幾聲,轉過頭不再看她,而是道:“若她親手将我折磨死,再自殺,也算合為一墳了。”
沉萱望着他背影,一時失語。
那日明無塵從她的觀劍亭下山,滂沱雨幕,她的劍奴原本護送着他,然而卻盡皆杳無音信,殒命當場。到了午夜,她察覺事情不對,出門去尋,見到謝師姐站在觀劍亭外,擦拭長劍,靜靜地等她。
沉萱窺見她劍上的血跡。
謝風息說:“師妹,你那未婚夫的身段,十分不錯。”
沉萱道:“我真該殺了你。”
“可你不會。”謝風息走近幾步,繞着她漫步一周,道,“你根本不愛他,你只是愛你自己,所以才稍微對這個體質純淨的正君好那麽一點兒,可要是你有了別的選擇、更好的選擇,你還會惦記着他嗎?”
沉萱的目光随着她動作而偏移。
“你殺了我,清源劍派的勢力便會小一分,對你報仇就更無益了,要是我将你的身世告訴魔尊,你說他會不會一時興起,來永絕後患呢?”謝風息笑道,“師妹,只要你将二郎許給我,不僅掌門之位是你的,我還會為你尋找更好的男修助你修行,我這個師姐,也甘心臣服,任你驅馳。”
“為什麽?”沉萱問。
“為什麽?”謝風息重複一遍,忽然揚唇大笑,差點笑得直不起腰,她的手搭在沉萱肩上,眼睛眯起,輕盈地道,“上有孟師姐,下有你,我雖然入了元嬰境,可前途無望,還不如去死。沉萱,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你究竟搶了我多少東西?不過也罷,你是我師妹,我照料你是應該的,以往我都不計較……只不過這一次,也讓我看看你的人,究竟是什麽滋味吧。”
沉萱難以理解她。
“我求道中途,受困在此,只想尋歡作樂。”謝風息笑着道,“你知道最讓我高興的是什麽嗎?就是把他按在懷裏時,他哭着喊你的名字,向你求救,可是沉師妹,你卻救不了他。”
沉萱默然片刻,似乎思考了許久:“我要你好好待他。”
“放心,我會讓他重新喜歡我、愛慕我的。”謝風息走近幾步,手指輕輕撣了撣沉萱的衣衫,諷刺道,“師妹,我早就說過,你只愛你自己,真是個僞善小人。”
沉萱後退半步,語調冰冷:“那你呢,瘋女人。”
這些年以來,即便在孟師姐面前,她們兩人都是貌合神離,更何況在私下,沉萱就更不會去主動打聽謝風息的事情了。
此事她雖牢牢記得,但卻難以宣之于口,只能緘默,過了半晌,才忽然道:“二郎,我替你殺了她。”
明無塵并未感動,只覺得這是一種根本沒意義的憐憫,他道:“有朝一日,我自然會親手殺了她,也會親手殺了你!在我眼裏,她雖然不可理喻,萬死不足洩恨,但你也一樣,跟謝風息沒有什麽不同。”
說罷,他便重新放下面紗,不願意再看沉萱一眼,而是躲在賀離恨身邊,靠在賀郎君身邊流眼淚。
賀離恨剛想要規勸他,為這種人流淚不值,仔細哭壞了眼睛,話還沒說出來,一旁的小惠便道:“主君放任他吧,人總有發洩之時。”
賀離恨先是點頭,而後又扭頭看着小惠,目光疑惑,今天的小惠姑娘居然主動開口說話了?
可他目光轉過去,小惠卻目視前方,臉上胭脂紅豔,唇紅齒白,目光跟陶瓷人偶一樣,莫得感情。
明無塵不跟她動手,一旁的孟琨玉卻按捺不住,她快要被這兩個師妹給氣死,要不是已經返老還童,打不過沉萱,恐怕現在就能清理門戶。
即便打不過,孟琨玉周身也劍氣凝聚,彙成令人膽寒之氣,幾乎一劍就能讓沉萱重傷。而站在不遠處的昆吾劍仙卻眉睫未動,合手躬身,向師姐請罪。
這劍光将出未出之際,一道滾滾清光籠罩而來,将無盡鋒芒按下去,一個清朗男聲從外響起:
“萱娘走得太急,我原以為是結姻親之好的清源劍派出了問題,所以趕來相助,沒想到遇見孟前輩動怒,只是萱娘再有錯,也是憐衣的妻主,孟前輩豈能揮劍說斬就斬呢?”
話音在殿內反複回蕩。
清光一卷,劍意鋒芒仿佛被無形的波濤裹挾着,化剛為柔。一個男子站在沉萱身側,親昵地挽住了她的手。
這位正是沉萱的正君,無極真君魏憐衣。
憐衣此名出自于一句描述夫妻恩愛之詩,說是一對道侶成婚百年,夫君壽盡之時,身形纖瘦,弱不勝衣,他的妻主在床頭榻尾照顧左右,不離半步,夫君死後,妻主也大病一場,跌落了幾個小境界,見到夫君的故衣,便情不自禁、潸然淚下。
魏憐衣的年齡比沉萱要大幾分,但也是芝蘭玉樹,氣度不凡。他站在沉萱身側,不僅外貌相配,似乎還能給予沉萱無限的支撐與後盾。
孟琨玉道:“她是我的師妹,我要教誨她,還需要經過你的同意?!”
魏憐衣先是對沉萱低語幾句,随後擡首道:“這未必就是萱娘的錯,何不等謝元君歸來,詢問清楚再說?就算萱娘一時不察,耽誤了這位……嗯,二公子?那也是她心中愛慕憐衣,不負憐衣的緣故,請孟前輩海涵。”
這話別說孟琨玉了,就是賀離恨聽着都感到無語,他審視着這個四年找段歸七八次麻煩的無極真君,喃喃道:“腦子裏只有戀愛嗎?還是只有自己的妻主?這昆吾劍仙也不像個會說話的……”
他堅定地覺得,自己被梅問情蠱惑,是她嘴甜溫柔,手段高明,陷入這種人的羅網,屬于是一時不察,情有可原。
但被沉萱這樣的蠱惑了腦子,那就有點……說不過去了吧……
魏憐衣可不知道他在想什麽,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逼問了數次、被确定已死的前任魔尊就在此中,此刻仍面帶笑意,一派溫和,語調如沐春風地道:“孟前輩,既然你這裏客人也多,不如我們坐下喝一杯酒,吃點東西,慢慢從長計議吧。”
他喚一聲孟前輩,那是禮貌,孟琨玉就是再怒火難消,但她自家人知自家事,她這種情況,又能撐幾年呢?只得給無極真君面子,緩和冷硬的神情:“如此也好,真君你其實也該好好盡盡自己的本分,規勸一下你的妻主。”
魏憐衣行了一禮。
這極為僵硬的氣氛,居然就這樣緩和了下來。孟琨玉用手掐了一下眉心,吩咐弟子道:“你們接待一下客人,等謝風息那個孽障回來。”
周遭劍修領命而去。
一時半會其實等不到謝風息。
梅問情心知如此,卻不多言。她與賀離恨共坐一席,姿态親近,一看便知是一對佳偶,仿佛對清源劍派的“家事”絲毫不過問,只是在茶點上用工夫,給賀郎挑點好吃的。
賀離恨胃口不好,吃不下這些甜膩東西,然而梅問情如此關心,他實在不好意思不吃,皺着眉頭嘗了一點兒。
她問:“有沒有喜歡的。”
賀離恨誠實搖頭。
“你這嘴巴越來越刁了。”梅問情道,“這讓人怎麽養得胖?”
她說完此話,便又靠近他耳畔,輕聲低語:“你說,這個魏憐衣實力如何,打不打得過你?”
賀離恨擡眼望去,見她遞過來一杯白水,便舉杯輕啜,端詳着對面跟孟琨玉商議的無極真君魏憐衣,他思索片刻,道:“如無意外,能讓我謹慎在意的,只有那把昆吾劍。”
梅問情道:“好,那一會兒我來找他的麻煩,咱們想辦法動手,不說殺了他為段魔君報仇,也得給他點顏色看看,讓這人知道咱們魔尊不是好欺負的。”
賀離恨看過去:“咱們魔尊?”
梅問情先是“嗯”了一聲,然後恍然大悟想起自己不是魔修,嚴謹修訂道:“我的魔尊。”
賀離恨哼了一聲:“我怎麽不見你有半點高潔偉岸的樣子,你真是正經的道門正修嗎?還是說,你只是功法充充樣子,實際上是什麽旁門左道。”
梅問情嘆道:“身具陰陽二氣,自然是參詳的先天陰陽大道,我可是真金不怕火煉、純粹無比的道門正宗啊。我不愛殺生的,難道你不知道?”
是,你不愛殺生,只愛看熱鬧罷了。
賀離恨瞥了她一眼,反正也習慣了,懶得說什麽,正待他琢磨着一會兒怎麽動手時,不知不覺中便将杯子裏的白水飲盡了,正當他考慮到一半,忽然覺得這水居然回甘,舌頭上都泛着甜,而後又有一絲甘冽辛辣。
“……這是酒?”
“酒?”梅問情也倒了一杯,稍微嘗一口,“不是水嗎?”
兩人四目相對,大約片刻,遲緩的甜味從舌根上蔓延過來,梅問情才慢慢地道:“……有點,難喝。”
賀離恨将杯子放下,然後又推得遠遠的,準備跟守殿弟子問一聲有沒有茶,然而還沒說出話來,就覺得一陣頭暈,他擡手捏了捏眉心,覺得自己的酒量不至于此。
一杯而已,這酒跟水一樣,能有什麽勁兒。
賀離恨眨了眨眼,松開手,道:“沒事,才一杯……”
他的嗓音被酒水浸潤,有一股軟糯感,尾音又透着輕微的啞,結果剛說出兩個字,就倒了下去。
“哎,你。”梅問情趕緊接住他,将賀離恨抱了個滿懷,向自己懷抱內側攏了攏,她擡指挑起他的下颔,見對方真的醉過去了,簡直有點難以相信,“這就醉了?這不就是水……賀郎?”
這頭的動靜不大不小,正好惹來孟琨玉的注意,她正跟魏憐衣商議得心煩意亂,于是先撂下這人,轉而問:“道友,這是怎麽了?”
“勞煩孟道友為我們準備一間房。”梅問情道,“你們這酒……真是普渡衆生、慈悲為懷,厲害,厲害。”
要不是賀離恨喝醉了,這時候應該跟他們打一架才是。
孟琨玉沒能意會,目露茫然:“這是我派的大夢浮,酒性極淡,引人磨練心境、了悟紅塵,怎會飲醉呢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