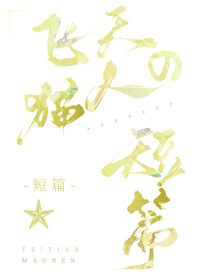擺在面前又是一個繁複的分叉口,兩條長廊和一條鵝卵石小路,每條路都像是通往宴席的道路,就算已經沿着來時的方向走了一炷香的時辰,但還沒有見到出口。
賀離恨緊握她的手:“這是她設的局、做的圈套,城主恐怕根本就沒有稀有靈藥為賞賜。”
梅問情道:“就算沒有了靈藥,能拿下蠍娘娘的鬼珠,打碎做藥,也算不虛此行。”
賀離恨扭頭看她一眼,心想這話一聽,還以為你才是那個招搖過市的鬼王魔頭,這人一身清淨、沒有半點怨邪之氣,怎麽說出話來卻随心所欲,他以前遇到的那些道門修士,無論男女,大多都要為利益扯出個大義來做幌子,聽着才好聽。
梅問情主動回叩他的手,伸手撩過賀郎的鬓發:“要是找不到關竅,咱們兩個不僅找不到狐仙兒,還要被困死在這裏了。”
蠍娘娘正是打着“甕中捉鼈”的念頭。
梅問情說完此言,忽然擡頭看向他身後,僅僅是一個眼神,賀離恨便心領神會,揚刀轉腕,向後揮去,正好将一只從後飛竄偷襲的食客劈飛出去,那頭鬼從相反方向來,慌不擇路,見到這“惹怒”蠍娘娘的兩人居然在這裏,竟生出了捉拿他們獻給鬼王,以求活命的念頭。
然而賀離恨在宴席上那一手,早已令無數鬼物清醒退避,所以才只遇上這麽一個蠢貨。食客受了魔氣一劈,叫聲驟止,化為一地污血。
魔氣在地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,不遠處忽然傳來一陣似人腳步聲和嬰童哭叫,那個名叫小婉的蒙面女的聲音響起:“捉回這些食客,娘娘被那巡邏使暗算受了重傷,急需大補,還有那兩個人,一定要抓活的回去……”
旁邊鼓童鬥嘴道:“我就要殺了他們!”
曲折回廊、數個轉角,才聞其聲,梅問情就拉着他鑽進了長廊邊上一列列的屋子裏,這些屋子破舊逼仄,裏面堆滿雜物,像是那群傀儡所住的地方。
梅問情伸手将單薄的窗紙稍稍戳破,不久後,孔洞便映出了蒙面女的黑裙。小婉身後帶着一衆傀儡,本該急匆匆在這裏過去,卻發現了地上那灘污血。
“這是誰動的手?這些家夥逃命之中,居然還自相殘殺。”鼓童趴在小婉的身上,童聲童氣地輕蔑道。
蒙面女也停在這裏,她僵硬地扭動脖子看過去。
這間房屋十分窄小,兩人躲在床後窗前,旁邊有許多雜物遮掩。因地方很小,賀離恨便被她抱在懷中,怕碰掉了東西弄出聲響,所以未曾輕易亂動。
兩人氣息相纏,一冷一熱,漸漸地繞轉在一起。她的呼吸涼意滲透,冷霧一般,清冽地帶着些許香氣,如此擁抱之下,梅問情的唇便不可避免地依稀碰到他的耳尖。
賀離恨抓着她衣衫的手略微收緊。
“魔氣……是魔氣……”小婉重複,“那兩個活人在這殺了它。”
“那兩個活人?哈哈,我們快去找!快找到那個女人!”
“這血液尚且新鮮,我們分頭行動,朝兩個方向去找。”小婉道。
鼓童哼了一聲,從她肩上跳到一只傀儡身邊,蠍尾刺進了傀儡身軀中,少爺做派地操控着這些傀儡向前方搜尋而去。
腳步聲響起。
梅問情眉目平靜,一言不發,但手心卻按在他的脊背上,目光穿過雜物盯着房門。就在賀離恨伸手欲提刀時,她卻沖着對方搖了搖頭,将蛇刀從他手中提出。
賀離恨自知久傷不愈,再交手恐怕又添新傷,可他更不願意梅問情動武,神情有些急切。但這魔蛇卻絲毫不給主人面子,被她的手一點撥,就迅速叛主,爬到梅問情的身上去了。
賀離恨盯着她,欲拽她的衣袖,可梅問情卻安慰似的低頭親了親他的臉,哄小孩兒似的讓他安分。就在靜默無比的此刻,外面的小婉道:“這裏也要搜索,你們去那幾間。”
她将傀儡調派過去,随即走入了旁邊的一間屋子,挨個巡查。
此言一出,必然不多時就會進入這間房屋。賀離恨心急如焚,盯着她的眼睛,滿臉都寫着“快把刀還我”。
蛇刀只有主人使用,才可發揮出其無可匹敵的銳氣與實力。更何況梅問情一身異術,卻無魔氣,賀離恨實在不願意讓她再用拘神。
小婉從旁邊的房屋出來,腳步從遠至今,片刻,她伸手推開了房門。
房門響起輕輕的吱嘎聲,裏面陳設密布。蒙面女粗略看了一眼,并沒見人,她似乎也沒覺得兩人真的會躲藏其中,所以又轉而打開衣櫃。
櫃門敞開,蒙面女的後背暴露在外,防備不足。就在她毫無發現想要轉身時,猛地被一股幾乎無法抵抗的力量按住後腰,一個人的身形如鬼魅般無聲貼了上來,單薄的小刀從後繞過來,割裂肌膚,呲地插入她的胸口。
随着小刀破開她原本堅不可摧的皮囊肌膚時,一道金紋也順着她手中的簡單小刀流入小婉的胸口。
金紋穿胸而過,幾乎激起一陣白煙冒出。小婉腦海中猛地響起一陣神聖龐大的鐘鳴,梅問情的聲音在她耳畔響起:“赤地旱魃?你祖宗天女魁在我座下聽過道,怎麽徒女徒孫卻淪落到這個地步,反而給鬼物效力。”
小婉真身即是一尊赤地旱魃,被蠍娘娘降服後才效命麾下。
小婉瞪大雙眼,驚懼交加,仿佛将旱魃為數不多的情緒統統湧現,下一瞬,她的大腦頃刻被奪走所有思緒感官,宛如旁觀者般,完全被另外一股強悍無匹的力量奪取控制權。
随後,另一道聲音驟然間在小婉的腦海中隆隆響起,帶着雷鳴般的回響,語調驚詫:“……師尊?”
梅問情怔了一下,沒想到自己就是提一句名字,千山萬水兩界相隔,都能把天女魁叫出來,她嘆了口氣,沒好氣地道:“我正要用禁制燒了她,你出來幹什麽?”
小婉早已力不從心,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自己轉過身,向面前之人行師徒之禮,她為數不多的智慧徹底失聯,朦胧依稀地想着:這究竟是不是真的魁祖?可是能随意操控所有赤地旱魃的,除了魁祖還能有誰?
天女魁也同樣意外震驚,呆滞不已,沒想到居然真的見到了她,差點喜極而泣,撲通一聲抱住了梅問情的腿,嚎啕道:“我還以為您不要陰陽天……唔嗚嗚嗚!”
梅問情一把捂住天女魁的嘴,冷着臉道:“小混賬,再叫就滾回去,少來煩我。”
天女魁這才作罷,她操縱着小婉的身軀,轉了轉僵硬的頭,眼裏充滿了孺慕之情:“您喚我是不是有事吩咐?”
梅問情将賀郎扶起來,把魔蛇交還給他,與此同時,那道離體片刻的禁制也重新回到身上,她輕描淡寫地道:“沒叫你,破壞我的興致。”
天女魁卻不舍得回去,她見到賀離恨被師尊如此對待,險些直了眼,又不知道是該叫什麽,只得悄悄試探着道:“這位是……”
“賀離恨,你叫賀公子就行了。”梅問情随便指了指天女魁,“這芯子裏頭的是我學生。”
賀離恨也大為震撼,他原以為對方一身拘神異術,已經足夠驚駭,沒想到她竟然還有這種能頃刻奪人心魂的學生,手段實在可怖詭異。
不等賀離恨開口,天女魁便率先道:“沒吓着賀公子吧,賀離恨這名……賀……”
她話語頓住,本就同樣不夠聰明的大腦又甩出來一個巨大的問號,陷入到迷惘震驚的旋渦當中——賀離恨?要是我沒記錯的話,近三五百年修真界正道諸掌門叫苦不疊、喊打喊殺的那個魔尊,不會就是他吧!
天女魁雖在梅問情座下聽過道,身為陰陽天宮之人。但她所領旱魃一脈,卻能與每一個旱魃心意相通,所以知道不少各界之事。陰陽天宮大多持正修心、不參與外事俗務,只有她對修真界的事知之甚詳。
魔尊?這人不是已經死了麽?那飄渺宗的老頭兒來報喜,還給陰陽天宮遞了不少帖子,只是這些隐世的祖宗少有人能請動,所以反應平平。
天女魁糾結不已,神情複雜,想到賀離恨離經叛道、狂言自負、親手弑母的傳聞,又見到他緊緊地握住了師尊的手,表情宛如一個混亂的油漆桶,那叫一個精彩,半晌才道:“在下之名……不值一提不值一提,污了賀公子的耳朵。”
師尊既在人間,想必沒有透露身份。天女魁最後這點心眼用光,也就完全沒掩飾住臉上的神色。
她的神情變化,賀離恨全部看在眼中,他心裏同樣咯噔一聲,想着梅問情多年游戲人間,不知道他正常,可看這個什麽學生的臉色,恐怕一報名字,此人便将自己的身份得知得一清二楚。
賀離恨自家人知自家事,他的名聲确實不好聽,裏面繁複冗長的內情沒人願意聽,大多都只領教過他的冷酷一面。從前他不介意,但如今……
他擡眸看了一眼梅問情的側臉。
這事兒絕不能讓她知道。
賀離恨表面上跟天女魁認識了幾句,眼神卻一直冰涼涼地盯着她,就在天女魁渾身不自在時,便見面前這個俊美郎君趁着師尊查看外面傀儡的動向,忽地改了神色,道:“閣下能耐出衆,我還真不敢相信你們只是修真界中的小門小派。”
天女魁道:“小是不算小,但人确實沒多少。”
賀離恨神情如冰,語調中帶着幾分寒意:“你老師只在人間,我不傷她,也不害她,我們平平凡凡相遇一場,你不必讓她知道我是誰。”
天女魁愣了一下,傷害她?
老師這一身禁制雖然是封印她自己,但也神鬼莫近、妖邪不侵,想要傷害恐怕很難。
她猶豫着不知道怎麽回,賀離恨以為此人遲疑,便擡手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,那條被交還回去的魔蛇悄然爬上,亮起尖牙。
“我不能殺你,不僅因為你身在修真界,更因為你是她的學生。但我可以毀了這具身軀,讓你在人間,永遠閉嘴。”
他的聲音很輕,似乎是不想讓梅問情聽到。
人美心狠!果然是這個魔頭無疑!天女魁先還在遲疑,這回完全确定,她第一次被男人威脅,卻也知道這人慣會跨越修為擊殺修士、且素有遇強則強、愈戰愈強的兇殘之名。她心說師尊的事兒果然摻和不得,表态道:“公子放心,老師的事我從不插手。”
主要也插不上手。
兩人短暫地一交流,不僅沒認識,還彼此提防起來。賀離恨越看這女人越不順眼,這種可能會對他和梅問情的關系造成傷害的人,就該在眼前消失。
天女魁心裏也不停嘀咕,這麽兇殘可怕、動不動就開口威脅的男人,一點也不溫柔,師尊真是……
兩人互看不順眼,可礙于梅問情的面子,都不言不語、假意和平。
梅問情從窗邊見那些傀儡搜完屋子,都排好隊等待小婉出去率領。她給天女魁一個眼神,道:“養徒千日、用徒一時,上吧。”
天女魁看了看自己的手,很是憋屈地道:“這尊旱魃修為低微,殺了這群玩意兒倒是簡單,但您說那個蠍娘娘,就算我拼死一搏,恐怕也……”
“誰說讓你殺了。”梅問情敲了一下她的腦袋,“聽課的時候就是最笨的,這麽多年居然還不聰明,你叫兩個傀儡進來,我跟賀郎扮成它們的樣子,回蠍娘娘的正殿。”
“回正殿?這要是出了什麽危險……”
天女魁話語一頓,看着梅問情。
梅問情也淡定地看着她。
這位魁祖呆呆地撓了撓頭,道:“我忘了,只要老師不動武,誰能動得了您呢。”
此言說罷,天女魁就咳嗽一聲,神态立馬和之前那位“小婉”一模一樣。她叫了兩個傀儡進來,這兩只詭異生物一進門,就被蛇刀割斷咽喉,倒在地上。
兩人更換了傀儡的外衣和面具,再加上梅問情手裏一點小小的障眼法,便跟随在小婉身後混入傀儡隊伍裏,神不知鬼不覺,看過去毫無破綻。
“小婉”領着傀儡隊向前,路上逮捕抓回了好幾個食客,随後不久便與無功而返的蠍尾鼓童碰頭,鼓童大叫道:“那兩個活人你也沒找到?!該死,竟然不知道跑哪兒去了,可惡可惡。”
天女魁心裏琢磨着這玩意兒到底是鬼,還是由人間鬼王用血肉催化出來的、外貌如嬰童的法器?她道:“你那邊捉回了多少人?”
鼓童身後的蠍尾紮入傀儡身軀,那只傀儡邊拎起手中粗壯的繩子,在繩索上纏着不少逃竄的食客,這繩索是那些“活線條”組成,将人捆住後動彈不得,胡掌櫃竟然也在其中。
狐仙兒精通幻術,可如今在人家的地盤上,人多勢衆,自然打不過鼓童。這蠍尾嬰孩洋洋得意道:“那頭帶着巡邏使的死狐貍也被逮住了,這回娘親肯定要誇我!”
天女魁敷衍地嗯嗯點頭,兩人便先将這些逮捕的鬼物送回去,給重傷的蠍娘娘補充鬼氣。有鼓童帶路,兩隊人很快便走出長廊,路過露天宴席,進入到了挂着白燈籠的宮殿當中。
宮殿裏輕紗拂面,處處是香爐、薄紗、珠簾,異香撲鼻。
大約一刻鐘後,兩隊人便走入正殿。此刻,一身黑色紗裙的蠍娘娘正卧在軟榻上,裙擺飄拂,她神色略有蒼白,長發散下,從腰部以下的地方都不是人身,而是一條巨大漆黑的蠍尾。
這條蠍尾被從中砍斷,墨跡飛濺,看來是巡邏使的手筆,蠍尾中滴滴答答地流着漆黑毒汁,落在地面上都嘶啦嘶啦地響,氤氲出升騰的霧氣,被毒汁包裹的血肉正在起起伏伏地湧動着。
蠍尾鼓童看見那些毒汁,兩眼發亮,它猛地跳了過去,趴在地上舔舐毒汁,又甜甜地叫着“娘親”。
蠍娘娘張口一吸,那些被捆縛的食客便盡入她口中,化為煙氣,只剩下胡掌櫃留在原地。她手中正攥着一截斷裂的筆,那筆狼毫炸起,筆杆都被濃郁的鬼氣包裹,在空中胡亂地寫着字。
而卷軸更是掉在地上,上面已經寫得密密麻麻、無處再落筆,無數的問題翻轉騰挪,互相調換位置。
梅問情猜想得不錯,這兩位巡邏使确實差不多因公殉職了。
蠍娘娘盯着胡掌櫃的臉,皮笑肉不笑地道:“好巧,胡家子孫,我們又見面了。”
胡掌櫃吞咽了一下口水,心中早就涼了半截,絞盡腦汁地搬救兵:“我胡三太奶統領北方域外,娘娘還是不要招惹仙家……”
蠍娘娘笑眼一彎,流露出狠辣冰冷的神色:“你以為你們保家仙還有多少威名?胡天花可都三十年不出世了,北方域外之地,我也遲早要掃清吞噬!”
她指了指天女魁,道:“小婉,過來給本王按按頭,疼得很。将這頭狐貍綁在殿中,慢慢折磨,我要讓她生不如死。”
天女魁身為旱魃之祖,在修真界又被稱為青衣天女,除了她巴結伺候都伺候不上的師尊之外,還沒被人這麽驅使過。她依言上前,心中卻憤憤地想,回去定要整治全族,為這等鬼物效力為伥,簡直是一種侮辱。
她的蠍尾血肉緩慢生長着,毒汁被鼓童舔舐幹淨。随後,另一個人撩開帳幔步入正殿,正是巫郎。
那巫郎先是看見了胡掌櫃,他斯斯文文地道:“女郎不在自家堂口盡力,來攪我妻主的事,就是有祖宗保佑,也無濟于事。”
他說完此話,便上前服侍蠍娘娘,在她耳畔說道:“你受了傷,千萬別動氣,那兩個活人一時找不到也沒什麽,我請柳先生上身尋人,連她也不知道在哪兒。”
蠍娘娘面露倦意,伸手攬住巫郎的身軀:“我累得很,只想着跟你雙修一回,才暢快些。”
巫郎臉色泛紅,又不敢推她,只得硬是任其解開了腰帶。他小聲地道:“雖沒找到那兩人,但柳先生卻找到了一個身帶蛛娘印記的男人,就在城裏。”
他說罷,輕輕拍了下手,便有傀儡将月郎帶上來。月郎一身淺色衣衫,被摁着跪在殿中,長發淩亂。
“月、月郎……”胡掌櫃瞪大雙眼,剛要掙紮,便被身邊的傀儡狠掐了一下,她怒目而視過去,而那傀儡卻只是面無表情地看着她。
月郎的衣衫被撕開,露出脊背上黑色的印記。他麻木地按住衣衫,倒是沒掉眼淚。
“還真是蛛娘的印記,原來是我那幹女兒的男寵,”蠍娘娘道,“可我幹女兒去哪了,不會連心愛的寵物都不要了吧?”
她一陣冷笑,又道:“長得倒是不錯,勉強可以替我那女兒盡孝了,把他弄過來,今夜也能為你分憂解勞,免得你受不住。”
巫郎侍奉她已久,沒說什麽,便讓傀儡将月郎架過來。小郎君白嫩柔弱,神情既不知畏懼,也沒有讨好,蠍娘娘鉗住他的下颔:“怎麽,連伺候女人都不會,還要我教你?你想死不成?”
月郎扭過頭,掙脫了她的鉗制,沒有看胡掌櫃,但卻說:“我不會在別人面前賣笑了。”
啪——
蠍娘娘反手打了他一巴掌,力道雖不重,可凡人身軀受不住,月郎倒在地上,牙齒磕破唇舌,沾了點血。
“把香點上,立什麽貞節牌坊,到最後都得是個蕩夫。”蠍娘娘冷道。
巫郎便起身點香。
這殿內本就異香撲鼻,再點一重香,更是甜膩無比,令人聞之頭腦昏沉。就在香氣馥郁之時,胡掌櫃忽然察覺捆着自己的繩子一松。
她擡起頭看着身邊的傀儡,而那傀儡仍舊面無表情地看着她,然後沖她眨了一下眼。
胡掌櫃:“!!!”
她燃起希望,又心急如焚地盯着月郎,要不是有梅問情摁着,恐怕已經按不住自己沖出去了。
就在蠍娘娘跟巫郎行雙修之法,情意漸濃,衣衫淩亂時,她身後靜默以待的“小婉”突然擡起頭,跟那隊傀儡對視一眼,下一刻,旱魃的手化為尖銳利爪,指骨彎曲不似人形,指甲如利刃般從後唰地捅下!
天女魁從背後突襲,蠍娘娘幾無防備。她被旱魃利爪從後背捅穿,自心口穿出,鬼氣大震,蠍娘娘甩起蠍尾,劇痛大叫:“小婉!你這個叛徒!”
她蠍尾一甩,龐大的帶毒蠍尾便漫天飛舞,毒汁流淌。巨大壯碩的尾巴橫掃過去,将旱魃打飛,蠍娘娘捂着心口的洞滾下軟榻,迎面便見到一柄魔氣森森、寒意徹骨的蛇刀——
賀離恨摘下面具,眸中只剩冷光。
砰!
蛇刀的鋒芒與蠍尾的厚甲相撞,劃出冒火花的劇烈聲響。
與此同時,胡掌櫃也立刻上前抱起月郎,帶他遠離戰場。這事态發生極快,那巫郎無暇管他們,閉眸請柳大先生上身,剛沖過去意欲幫自己的妻主,迎面便見到一串閃爍的金光。
梅問情擡指取下面具,撤下障眼法,她微笑着看向對方,雙手輕輕一扣,發出一道細微的響聲:“我知道你擔心她,不過我家賀郎不能久戰,我也擔憂得很,你就不要給他添麻煩了。”
她手腕上的金紋騰空浮起,在半空中飛快轉動,一道禁制的解除,她身上重新産生那股令人喘不過氣的壓力。梅問情語調溫和、很好說話地道:“柳先生,還是給我下來吧!”
金光轉動如輪,她話語仿佛帶着一股莫名的力量,言出法随般,聲調剛落,巫郎便感覺到自己身上的柳大先生仿佛被什麽力量剝落着。
他吐出蛇信,渾身劇痛,背後冒出一道蛇仙虛影,被金光纏繞住,瞬息間消失無蹤。巫郎倒在地上不停喘氣,渾身如同拆了一般劇痛。
梅問情用鞋尖擡起他的下巴,居高臨下,眉目淡淡:“叫你妻主乖乖送死,否則我宰了你。”
“她……嗬……”巫郎嘔出一口血,“她不會聽……”
她确實不會聽。
蠍娘娘劇痛瘋魔之中,已經失去理智,梅問情便擡腳踢開這個助纣為虐之人,轉身走向另一邊,她手上的禁制還未收回,淩空轉動的金紋放出了一股難以抵抗的沉重力量。
賀離恨橫刀擋住蠍尾,腳下被抽退十幾步,他與天女魁合力,雖力量上不能勝,但兩人的作戰能力卻超出鬼王千百倍,他見到梅問情放開禁制,分了些神:“梅問情,不許動武!”
天女魁道:“對啊對啊,老師我能——”
話沒說完又被鬼氣逼退。
他倆一個比一個能逞強,天女魁只是奪旱魃身軀下界,能力受到軀殼所限,傷倒是傷不到她身上,可賀離恨是實打實的舊傷難愈、不能久戰。
梅問情嘆道:“哎呀,我的賀郎,就算我出手助你,也不會多向你讨要報酬的。”
賀離恨氣惱不已:“我沒說這個!”
然而他卻阻攔不了,眼睜睜地看着梅問情身上映出金色光芒。那些禁制一旦放開,就如同放開了一股毀天滅地之力,而梅問情只是輕松撬開一角所用,氣息磅礴浩瀚,她步步走近,不忘玩笑道:“我知道你心疼我……”
蠍娘娘對兩人久攻不下,已然煩躁,她似乎感覺到了處境的危險,她的胸口流淌着漆黑毒汁,神情瀕臨瘋狂,掉頭就向梅問情沖去。
“你到底是什麽人?!”
她渾身鬼氣翻湧,蠍尾脫落的血肉如活得一般,上下湧動扭曲,纏繞成帶毒的肉鞭翻飛揮舞,但這些鬼氣毒汁在接近梅問情時,卻被她身上金光所攝,寸步不能近。
“我嘛,”梅問情看着她,眼中映出一輪陰陽魚,在眸中緩慢轉動,“我早已介紹過了,凡間的一位教書先生,敝姓梅。”
她手腕上的金紋禁制解開,陰陽二氣如旋渦般狂湧而來。蠍娘娘撞入她面前,仿佛撞進一團又一團軟綿綿的棉花當中,她雙眼與那輪陰陽魚對視,頃刻間消失了自己所有的思緒。
她感覺到有一雙眼睛看着自己。
那雙眼睛并不殘酷暴虐,也不兇悍陰森,而是純澈寧靜、返璞歸真,這視線強橫得讓人生不起反抗之心,在這雙眼的凝視下,她的記憶、心法、每一道細微至極的思緒念頭,全都逃不過她的眼睛。
仿佛一切都消失了。她所有的一切都被對方觀賞着、把玩着。
蠍娘娘仍能操控自己的身軀,但她想要說話,卻在下一瞬失去了說話這個念頭,想要動彈,卻在呼吸間忘卻了自己要行動,她的大腦已經完全浸泡在陰陽二氣當中,眼前只有一輪越來越大的陰陽魚。
咚——
沉沉的鐘聲從腦海深處響起。
這鐘聲龐大恢弘得令人敬畏,她的神魂仿佛随着鐘聲而去,伴随着恢弘的鐘鳴,她依稀不斷上升,望見了濃郁的雲霧,在雲霧之巅的最深處,見到一座橫跨穹宇的飄渺天宮。
天宮最頂端傳來一陣陣講道聲:“……其性不争、其人洞虛、其欲自然……莫能與之争……”
蠍娘娘幾乎沉淪進了這講道聲中,她腦海中不斷盤旋着一輪陰陽魚,黑白兩色盤旋不定,轉動得越來越快——而她兇殘的蠍尾本體,也受到節節陰陽二氣洗刷,逐漸澄明柔亮,化為一只小小的幼蠍。
它被洗去所有鬼氣和塵埃,變成了一只非常普通的幼蠍。
梅問情眼中的陰陽魚消失,而她半空中旋轉的金紋禁制也落回手腕之上,掩蓋在衣袖之下,她可惜道:“這麽不禁教誨。”
蠍娘娘腦海中跨越了千山萬水、九重天闕,可這些事實上只發生了兩個呼吸的時間。
梅問情輕咳一聲,不動聲色地将喉間泛起的腥氣逼回去,只是輕微蹙了下眉。她一擡眼,便見到賀郎那張嚴肅的臉。
賀離恨一言不發,先是拎過她的手看了看,上下審視片刻,才道:“……我能解決她的。”
“你若再受傷,可就沒人保護先生我了。”梅問情笑眯眯地道,“我這麽體恤,怎麽不見你誇,難道是看我搶了賀少俠的風頭嗎?”
賀離恨跟她鬥不起嘴,他深深呼吸,擡手半環住對方的腰,低頭将額心貼在她肩膀上,低低地道:“……不要這樣做。”
梅問情怔了一下。
“你要相信我。”他說,“你明明知道不能動武,卻根本不在意自己,梅問情,你為什麽照顧不好自己呢,你這樣我會覺得很……有點擔心。”
他語調輕微,最後半句聽不太出來是什麽,但以梅問情的耳力,卻能字字句句入耳入心,她擡手覆蓋住賀郎君的後頸,摩挲着指間的肌膚,附耳低語:“好孩子,說得我都心疼了。”
她擡手摸了摸對方的臉,賀離恨卻偏過頭,情緒仍不高:“不許這麽叫我。”
梅問情笑着逗了他幾句,而後摸着他的手,覺得比平時熱了些,突然想起什麽,一轉頭才看見那盞爐子燃着的詭秘甜香。
這香氣芬芳馥郁,狐仙兒野性仍在,早已抵抗不住,跟月郎在紗幔後頭滾作一團。梅問情将香爐潑水熄了,悄悄問賀離恨:“你若是難受就告訴我。”
賀離恨耳根紅得滴血,神情卻還故作鎮定自若:“我才沒有事。”
————
等狐仙兒跟月郎雲收雨歇,已經過去半個時辰了。
梅問情坐在殿中,手裏把玩着她抽取出來的鬼氣——這原本是屬于蠍娘娘的。這磅礴鬼氣被她捏成一個小小的黑丸,圓潤漆黑,只是不知配哪幾味藥材煉制,效果才好。
天女魁方才見師尊跟賀離恨那般情态,心裏更是百感交集、五味陳雜,她有點兒忍不住想提醒師尊:這男人不可信,他盡是僞裝,什麽實話也沒告訴你。
然而被賀離恨死死一盯,天女魁也不好開口了,更何況她轉念一尋思,知道師尊也什麽實話都沒告訴他,也有些別樣的安慰。
正在天女魁胡思亂想、百般擔心時,聽到梅問情開口道:“巫郎應該不至于說謊,福姬……鎮城之寶這聖靈之體,就縮水成這麽大點兒了?”
天女魁方才拷問巫郎,才随他前往密室找到了許州城的鎮城之寶,她起身回答:“禀告老師,我用搜魂看了他的腦子,這确實是福姬無疑。”
梅問情點了點頭,然後三人便繼續對着眼前這個四歲大點的啞女出神。
福姬身為城主之女,也是許州城的鎮城之寶,她被割去治療巫郎的那塊肉,就是她的舌頭。
此時,福姬已然傷痕累累,昏睡不醒,她身上的确力量微弱,別說群魔辟易保護許州城了,連能否活下去都在未知之數。
随後,一旁的帳幔撩開,吃飽喝足的胡掌櫃擺着一條大紅狐貍尾巴鑽進來,她攬着月郎,一擡頭,三人的目光便齊刷刷地看過來。
胡掌櫃尴尬道:“大家都在呢啊……”
梅問情幽幽道:“我們深入龍潭虎穴,費盡心思,你倒舒服自在,很會享樂。”
胡掌櫃頭皮發麻,扶了一下頭上被月郎扯歪的簪子,往濃黑的發鬓裏穿了穿,理虧道:“這事兒怨我,确實怨我……對了,你們是怎麽來的,這位是誰?”
她不說,梅問情還差點忘了,旱魃一族的魁祖日理萬機,豈能在此處空耗,她道:“此事已了,你回去吧。”
天女魁連忙道:“學生願在您身邊侍奉左右。”
梅問情也不表态,只是淡淡地望着她。
天女魁與她視線一對,立即心中一抖,不太情願地低頭道:“那學生告退。”
她想到那蠍娘娘竟能聽到老師的教導,卻禁受不住,升起一陣對鬼物的嫉妒,只可惜她沒有機緣,便抽取了小婉的一段神魂,囑咐了些許話語,才退回意識。
魁祖意識抽離,在一陣眩暈之後,真正的赤地旱魃小婉重新睜眼,她操縱身軀明顯比天女魁僵硬許多,低首候在梅問情身畔,似乎受到命令任其差遣。
蠍娘娘死後,那些因她誕生的蠍尾鼓童也盡皆滅亡,傀儡沒有鬼氣纏繞,盡皆失去動力,這樣一座夜間鬼城,頃刻之間便無法運轉。
小婉帶着幾人穿過重重長廊,離開了此地。那巫郎重傷不支、沉默虛弱,也不見反抗,踏出那白紙燈籠的界限時,晨曦的陽光才照射到眼前。
翻天覆地,區區一夜而已。
梅問情困倦不已,這些事的後續雜物都懶得管,交給胡掌櫃善後處理、聯絡朝廷。她則是進了歇腳的客棧,褪去外衣喝了口茶,就着晨光便蒙頭窩進被子裏。
看來是困得不行了。
賀離恨坐在榻邊,扯着被褥給她蓋上,扯了扯被角,然而從被子中伸出一只手,很不講道理地把賀離恨拉進被窩。
她的懷抱賀離恨已領略過許多次,但仍覺肌膚接觸之間,令人難以自禁。他的喉結稍微動了動,意欲起身,結果又被摁着肩膀抱緊了。
梅問情埋頭抱着他:“你不困,你是鐵打的,閉眼。”
這跟命令也沒兩樣了。賀離恨卻不生氣,他望着梅問情低垂的眼簾,睫羽纖長,細密如扇,沒有一點兒是不好看的,他說:“好。”
晨光從窗隙漏過來。
若說梅先生有什麽興趣,看書是一件事、睡覺是一件事,這逗弄賀郎就是頂頂重要的一件事。她才眯了一會兒,稍緩精神,一擡頭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