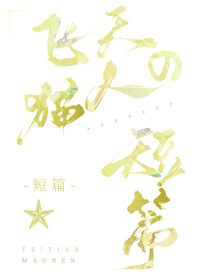他俯着身子, 一捋黑發垂下,落在藺绮微微濕潤的衣襟上,青年握着藺绮的手, 寫下幾個因為心煩而被她寫岔的字。
——“人能常清靜, 天地悉皆歸。”
常說字如其人, 放在仙尊身上并不大适用。
他性情溫和安靜,字體卻十分灑脫肆意,有一種掙紮而生的自由。
霜雪天裏沒有刀劍也沒有鮮血,柔和的陽光自窗子打進來, 像破碎的金粉。
藺绮垂着眼睫,看紙上緩緩寫出的經文,神情認真, 看起來很是乖巧。
堕魔之後, 這樣的經文對她來說沒有任何作用, 但容涯的出現依然讓她安心。
盡管現在的她是正道最厭惡的的魔物, 而身後站着的是正道仙門最負盛名的仙尊。
這時, 魔氣不受控制自指尖溢出。
藺绮眼睫微顫, 有些懊惱。
她動了動指節,想把洇出的魔氣蓋住,可是這魔氣狡猾得讓藺绮生氣,止不住地往外洇, 甚至漫上青年的指縫。
藺绮臉色一白,緊緊抿着唇。
容涯仙尊像是沒看見一樣,輕輕捏了下她的指尖, 說:“昨晚我在秘境裏, 那個秘境有點麻煩, 我花了點工夫才破陣出來, 耽誤那麽久實在是不得已。”
是在跟她解釋。
整個仙門都解決不了,被迫請仙尊出世的秘境自然是麻煩的。
淺藍色靈氣自指尖溢出,如冰霜般,凍住泛濫的魔氣。
“擡頭,我看看委屈了沒有。”容涯點了點藺绮的手背,讓她擡頭。
藺绮眨了眨眼睛,緊繃的神經乍然放松下來,積攢已久的委屈又如潮水般泛濫,之前被那麽多人苛責的時候,她不曾有過任何脆弱情緒,現在安全了,難過的情緒反而接連湧上來,情不自禁紅了眼角。
容涯拿冰涼的指尖抹了下她的眼睛,有些無奈地笑道:“怎麽委屈成這樣。”
“委屈了還不撕符,”他拿濕潤的帕子給她敷眼睛,語氣溫涼,不鹹不淡道,“不撞南牆不知道害怕,誰慣的毛病。”
藺绮偏了下頭,不看他,悶悶說:“別兇,誰把我養大的你去怪誰,他的問題。”
容涯怔了半晌,笑了一會兒:“你倒是很知道追本溯源。”
藺绮說:“不對嗎。”
青年啞然,深刻反省了一下自己,說:“也有幾分道理,我檢讨。”
藺绮忍不住笑了。
她笑的時候,目光糯糯,看得容涯心軟。
他放下濕帕子,看藺绮的眼角不再紅腫,又放出靈氣把她的發尾弄幹,讓她補一會兒覺,自己則拿了一冊書,臨窗坐着陪她。
短短兩日內發生了那麽多變故,藺绮早已心神俱疲,躺上床後沒一會兒就睡着了。
仙門識趣地沒有來霜雪天打擾他們。
唯一來的是藺浮玉,還是仙尊叫他來的。
藺浮玉依從仙尊的吩咐,帶來一束從鎮山神樹上摘下來的流蘇花。
他走進霜雪天時,望見霜雪天裏落英缤紛、生機盎然的景象時吃了一驚,後又想起容涯仙尊,思緒才定了定,如此大規模的四時陣法在他看來恍若神跡,在仙尊眼裏大約不算什麽。
藺浮玉走進高樓時,青年正在竈房裏熬粥。
霜雪天裏的竈房和人間的一樣,這還是藺浮玉第一次在臨雲宗裏看見這麽接地氣的東西。
乳白色的薄霧在空中蔓延,青年半倚着竈臺,拿着錾子在鈴铛型銀球上刻刻畫畫,動作認真細致。注意到藺浮玉,青年停下手中的動作,抹去銀球表面的銀屑,擡眸看了藺浮玉一眼,颔首示意他進來。
藺浮玉躬身行禮:“仙尊。”
“有勞你,”容涯語氣溫和,“會煮花茶嗎。”
藺浮玉不明深意,點頭道:“會。”
容涯點了點流蘇花葉,說:“勞煩。”
藺浮玉本來是來送東西的,稀裏糊塗留在這裏煮茶。
傳說鎮山神樹的花葉有一種極其玄妙的功效,可以靜心安魂,滌淨靈氣中的雜質,不過這只是藺浮玉聽說的而已,畢竟沒人敢真去薅鎮山神樹的花葉,這一次還是他跟神樹說容涯仙尊要,神樹主動給他的。
霜雪天裏的仙尊遠沒有主殿裏那般清冷壓人,青年慵懶倚着竈臺,垂首雕刻銀白鈴铛,看起來就像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清貴書生。
他不經意擡眼時,意識到藺浮玉的疑惑,說:“不必拘束,本尊又不會吃人,有什麽想問的直接問。”
“弟子聽說,神樹的花葉可以安魂靜心,純潔靈氣,”藺浮玉心有不解,“可是弟子沒有任何安魂靜心的感覺。”
藺浮玉說完,又猜測:“或許泡茶飲用之後才有如此效用。”
容涯莞爾笑了會兒,垂眸在鈴铛上刻花,語氣清溫:“你喝一口就知道了。”
藺浮玉問:“可以嗎。”
青年點頭。他看着藺浮玉,眼中沒有白日裏的冰冷和高高在上,反而是帶着笑的,就像一個脾氣很好的同齡人,耐心等着藺浮玉的反應。
藺浮玉捧起茶盞抿了一口花茶,這茶還沒來得及放糖,入口還帶着茶坯的清苦。
茶水入喉,藺浮玉嘗試着運轉靈氣。
體內靈氣沒有任何變化。
這和傳言中很不一樣。藺浮玉遲疑着,容涯略偏了下頭,将一袋冰糖遞給他,道:“本就沒有你說的那些作用,這些花葉的用處在驅魔除祟,你若是堕魔了,喝了這個可以清醒一些。”
“加三塊糖。”他說。
“這是給袖袖的嗎?”藺浮玉意會,他頓了一下,一顆心提起來,問,“仙尊,除了烏山剔骨,還有別的法子拔除魔骨嗎。”
“袖袖?”容涯琢磨了下她的稱呼,安靜看了藺浮玉一會兒。
心想,袖袖的親哥哥啊,這樣喊也并非不能接受。
青年垂眸,目光虛虛落在乳白色水霧裏,說:“沒有別的法子,但會剔骨的并非只有烏山。”
他說着,輕哂:“多少年了只會這一招,真是不長進。”
藺浮玉不明所以,卻隐約意識到仙尊的愠怒。
他離開前,問容涯主殿外的弟子們該如何處置。冰柱還沒有撤下,至今沒人敢走。
容涯摩梭了下鈴铛,漫不經心道:“寒冰獄裏跪三天吧。”
別說在臨雲宗,就算是全仙門,都很難找出比寒冰獄更難熬的地方,寒冰獄裏跪三天,降一個境界都是輕的。
……
夜裏,月上中天,綴滿白花的樹枝擦着窗子伸進來,花枝上盈滿月光。
藺绮睡得并不安寧。
她像是跌進一場迷茫大霧。
煙霧漆黑,伸手不見五指,陰森的氣息像一座囚牢,死死罩着她,無數冷槍暗箭射向她,鮮血滴答滴答落下來,輕而緩慢的聲音冰冷得讓人發瘋。
長久以來積壓的惡念如瘋長的枝桠,一下一下抽打她的心髒,腦中無數個嘈雜的聲音交錯在一起,斥罵、詛咒、蠱惑……
藺绮的情緒近乎崩潰了,她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往前跑,刺骨的冷風呼嘯而過,忽而,她腳下踉跄,跌入一個清冷的懷抱。
藺绮睜開眼。
青年坐在床頭,伸出指尖輕撫她的眼睛,他照舊一身素白,身上有月光的清冷味道。
藺绮眼睫微眨,覺得眼睛有點幹澀,迷糊問:“我在哭嗎?”
容涯嗯了一聲,把藺绮扶起來,攬在懷裏。
藺绮趴在他肩頭,說:“姐姐,你剛剛是不是走了。”
青年眼簾輕垂,應了聲是:“我疏忽了。”
袖袖小貓蹭蹭他的肩窩,她剛做了噩夢,現在沒什麽安全感,聲音悶悶的:“姐姐,不要走,我害怕。”
“不走。”容涯喂了她一點流蘇花茶,藺绮才清醒了些。
他端來熬好的蓮子粥,一勺一勺喂到藺绮唇邊。
粥被熬得爛稠,還帶着蓮子的清香。
她吃飯的時候素來是乖巧的,哪怕堕魔了,看起來也十分溫良無害。
她自認為僞裝得很好,乖巧溫順,和平日并沒有什麽不同,但到底是一手養大的,容涯還是能輕而易舉看出她的不安。堕魔對他而言不算什麽,但袖袖年歲太淺,害怕也在情理之中。
藺绮喝了一碗粥,胃裏舒服了些。
青年揉揉她的長發,說:“我幫你剔骨,不會很疼,只是催動魔骨時,你的意識可能會不清醒,不用害怕,我在這兒。”
藺绮一怔:“現在嗎。”
“嗯。”
他握住藺绮的手。
淺藍色靈氣自指尖流出,沒入藺绮的身體,青年的靈氣和他的人一樣,溫柔且純粹,沒有一絲雜質,流入軀殼時,藺绮只感到靈池清淨,舒展暢懷,就像于熾熱盛夏接觸到了陰涼井水,給人一種難以言喻的享受。
藺绮懶洋洋眯了眯眼睛。
他似乎不知道林守在她靈池上加了卦陣,可以讓她保持清醒。
藺绮眼睫覆下,目光落在青年的手上,有些出神。
清瘦修長的指節,蒼白的手背,借着月光,隐約可以看清手背青藍色的血管。
很漂亮的手,手心、手背、手指,哪裏都漂亮,很适合拿來親吻,如果這雙手的主人不生氣的話。
藺绮正胡思亂想着。
忽而,容涯指節一緊。
藺绮的手被攥得生疼,青年像是意識到了,克制地松了力道,再看,剛剛被他握住的地方,已然一片通紅。
“對不住。”他的聲音有點啞。
青年臉色蒼白,呼吸愈發地輕,額上也滲出冷汗。
藺绮覺得古怪,忽而想起剛剛喝的流蘇花茶,她第一次喝流蘇花泡的茶,這茶水的味道和之前喝的都不一樣,細細一想,似乎還有花茶之外的味道。她望了望桌上還沒喝完的茶水,茶水裏飄着符紙的碎屑。
藺绮自己就是符師,耐下心來仔細辨認,自然知道那裏面加了什麽符。
——換生符。
作用只有一個,就是疼痛轉移。
難怪她不疼。
認真想想,魔骨早已成了她身體裏的一部分,剔骨怎麽可能不疼。
藺绮倚在青年懷裏,指節微動,畫了一個符文打在自己身上。
青年驚且怒,斥道:“鬧什麽。”
藺绮所有的符術都是他教的,想要阻止她的符文只是擡擡手指的事。
他分出一縷心神,驅散藺绮的符文。
剔骨一旦開始就不能中斷。
淺藍色靈氣一點一點削離骨頭上的黑霧,其痛苦不亞于淩遲。
劇烈的疼痛如狂風驟雨打來,青年臉上一點血色都無,險些坐不穩,踉跄了下撞上床頭,玉冠落地,烏黑長發如瀑垂下,碎發半遮住青年的眼睛,發尾被冷汗打濕。
藺绮又想些做什麽。
容涯把她圈在懷裏,聲音輕而模糊,低低道:“別鬧,再鬧你就沒姐姐了。”
他嗓子微啞:“袖袖。”
藺绮抿了下唇。
銀白的月光在空氣中浮沉流轉,一陣風送來梨林清靜而素雅的花香。花枝探進窗子輕輕搖晃,抖落一桌的白花。
天地靜谧,星月無聲。
藺绮反叩住容涯的手,微微擡首,吻上他的唇。
她學着在書上看到的渡靈氣的法子,生疏地把靈氣送出去。
容涯怔住。
她又慌亂又緊張,親吻很不得章法,小貓撓人一樣,對着青年的唇又啃又咬,她閉着眼睛,纖細的長睫一顫一顫,伸手抱住他的脖頸,溫軟指尖在青年冰冷的脖頸上來回游移。容涯垂眸,還能看清她唇上沾的水漬,這水漬還帶着流蘇花葉的清淡香氣。
青年指節收緊,似是不能忍受,阖了阖眼睛。
真要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