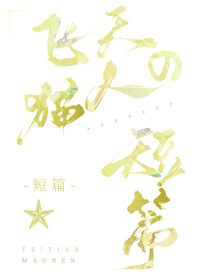手背撞在床榻上, 許幻竹有些吃痛,皺着眉嘟囔了一句:“幹嘛呀!”
過了片刻,迷迷糊糊間又聽見頭頂傳來一道聲音, “這玉墜子已經過了時,沒什麽好的, 我拿好東西跟你換好不好?”
好似帶着些蠱惑意味。
聽見清淩淩的鈴铛音,她緩緩扯開一絲眼皮, 眼前是一根彩色的手繩。
編織手繩的繩子看着細膩柔軟, 顏色鮮亮, 中間綴着一枚小巧的銀鈴铛。
底下那個穗子, 是翠色的。
看着許幻竹盯着手繩的亮晶晶的雙眼,時霁眼中也蒙上一層笑意。
他就知道, 許幻竹肯定會喜歡。
他撥了撥那手繩上的鈴铛, 低聲喊她:“翠翠?”
“嗯?”許幻竹茫然擡眼。
“換不換?”他又欺近幾分。
雖然這手繩很好看, 但墜子她是要還給淩清虛的。
許幻竹一把推開, 拒絕道:“不換。”
“不換?”
“不換!”
這兩個字再一次落下, 時霁眼中的笑意瞬間暗下來。
煙青色的床幔子突然動了動, 從他耳側掃過,他一動不動地坐着,那瞬間的安寧祥和宛如雪崩前的大山。
而雪崩之前, 沒有任何一片雪花是無辜的。
這時候,桌子上的綠毛鳥也跟着添堵,撲了撲翅膀沖着時霁喊道:“不換、不換!”
時霁摘下許幻竹耳間的一只白玉墜子,朝着那綠毛鳥的方向砸了過去。
它被吓得嘩啦一下往上飛起,撞到籠子頂上, 發出一道撞擊聲,又暈乎乎地落下。
房中瞬時又恢複了安靜。
不換?
許幻竹這樣記仇的人, 淩清虛那般欺她騙她,她還這般寶貝着他送的東西。
仔細收起來放在妝臺上不說,連醉成這樣也死死護着。
呵。
真是好樣的。
時霁将手繩塞回了懷裏,鐵青着臉猛地起身往外走。
屋子裏沒點燈,他才走出兩步,一下撞在妝臺上,又一下撞在凳子上,發出一陣叮兒咣當的響聲。
他面不改色地走到了門口,打開門一腳邁了出去。
時霁走後,桌子上的翠翠才敢慢悠悠地站起來,正想喝口水壓壓驚,卻看見籠子裏裝水的碗被打翻了,它還沒來得及去啄那最後幾滴,外頭那人又折返回來,它吓得又立馬倒下。
時霁走進屋子裏,走到那方桌前,借着門外的月光,他撿起落在地上的耳墜,這才關上門離開。
聽風等雪酒館裏,柳山齋一人仰躺在椅子上,桌前酒杯倒散,一片狼藉。
山裏的夜都涼,這時候屋子裏門扇大開,外頭的夜風吹進來,柳山齋生生被凍醒。
他晃晃悠悠擡起頭,只見左右都無人,許幻竹和時霁不知去了哪裏,只剩下自己一個。
“這兩人怎麽回去也不喊我,真是沒良心。”
他繼續倒在椅子上,末了擡頭又喊了一句:“好歹給我把門關上啊。”
-
許幻竹醒來的時候,已經是半日下午了。
嗓子裏又幹又苦,她掀開被子下了床,拿着桌上的水猛灌了兩口。
翠翠在籠子裏蔫蔫地盯着她。
許幻竹扶起翠翠的水碗,往裏倒了些水,好笑道:“你怎麽把自己喝水的家夥都打翻了?”
翠翠嚎了一聲表示不是它幹的,然而許幻竹只是十分鄙夷地看了它一眼,那表情似乎在喊它‘傻鳥’。
“這都是我幹的?”看了看亂糟糟的屋子,許幻竹滿臉疑惑。
于是扶正被撞歪的妝臺,順手拉起腳下倒了的凳子,往外面走去。
腦袋還有些昏昏沉沉的,于是換了個地方坐着,坐在了院子裏的竹床上。
昨日從秘境裏出來,她一路顧着早些回來,不能被那幾個弟子看出端倪,反倒忘了件事。
她從懷裏摸出一張通訊符,指尖微動,符咒亮起。
不一會兒,那邊傳來一道細小的女聲:“許仙長?”
許幻竹捏着通訊符清了清嗓子:“玉珍啊,是我。你身邊可有旁人?”
那一頭回道:“就我一人,仙長可是有什麽事?”
“在青雲秘境的第一日,你在那洞裏被夢魇困住的事情你可還記得?”
“當然記得,若不是仙長,玉珍可能就要困在那洞裏了。仙長現在找我,可是那秘境中有什麽古怪?”
“是,我的确覺得這一次的青雲秘境不同尋常。”
且不說範玉珍那一次,後來時霁在那樹下被困住的那一次更是古怪。
青雲秘境中的試煉,從來都是以提升弟子們的法術修為,應變能力而設。就拿她從前參加的那一次來說,入秘境的弟子從來都是各憑本事,去打通一路設下的機關阻礙,或是埋伏的沙石精怪就好。從前打架是她的強項,這也是她當年能那麽快走出秘境的原因。
但如今這秘境的設置倒是有些奇怪,像這般幾次三番窺探人心,以心魔夢魇做試煉的,倒是聞所未聞。
這一群弟子裏,心思最重,經歷得最多的,也只有時霁了。
只怕是有什麽人從中作梗,想要接着這一次的秘境試煉,做些什麽見不得光的事情。
許幻竹繼續道:“這事情我不方便出面,玉珍,麻煩你将你在秘境中被夢境困住的事情告知你師尊,他會告訴儲殷。”
“好,玉珍一定将話帶到。”
放下這傳音符,許幻竹瞥見袖子口上沾上點點紅色,似是血跡,極小的一塊。
奇怪,從哪兒沾上的?
許幻竹甩甩袖子,順手施了個清潔咒,施法時,袖子裏忽地飄出兩張紙來。
她拾起看了看,上面寫的是她明日去淩虛宗要講的東西。
這……好像是昨夜時霁給她的。
宿醉過後的腦子不太清醒,只隐隐記得時霁背着她回來的路上給了她這兩張紙,後頭回了屋子,好像還發生了些什麽。
她揉揉腦袋,竟全然想不起來了。
于是幹脆不再想那些,翻開那兩張紙仔細看了起來。
這午後的陽光灑在身上,讓人覺得舒适非常,暖和的春風吹着,也十分惬意。
後來也不知才看了幾行字,許幻竹這上下眼皮子又張不開了。
她又想到,這這時候,裴照雪應當該出來嘲笑她了,怎麽如此安靜。
不過說起來她的确是好久沒出現了,她還以為之前是因為她變作了翠翠的樣子去了青雲秘境,才沒有聽見裴照雪在耳邊念叨。
可她現在她回來了兩日,按理來說,她也該出來一回了。
難不成真如裴照雪說的那般,她離開焚山太久了,氣息越來越弱了?
管她呢,這人沒了才好,叫她耳根子都要清淨許多。
她巴不得她再也別出來。
‘咚’的一聲,許幻竹終于堅持不住,一頭栽了下去。
躺下的那一瞬她還在心裏念叨:就眯一會兒,半柱香就起來。
于是手裏的那兩張紙被風吹開,一張落在竹床下,一張翻在花叢裏。
許幻竹此時并不知道,她睡得正香甜。
後來日頭漸漸西斜,滿院子的月見草随風輕搖。
粉色的一朵朵在光影裏探着腦袋,許幻竹的衣角從竹床上落下來,搭在花叢裏,也跟着一起搖搖晃晃。
因着明日要去淩虛宗,所以今日的課業早早地就結束了。
時霁從青雲天宗回來的時候,便只看見這麽一副情景。
許幻竹仰頭睡在竹床上,長長的頭發順着後頸垂下,散在腰側。
她一只手搭着竹床邊緣,袖子被勾住,垂下來一只小臂,指尖都快要落到了地面上。
另一只手搭在自己腰上,大拇指與食指撚在一起,保持着奇怪的姿勢。
桃樹漏下斑駁交錯的影子,落在她身上,波光粼粼。
他看見草叢裏被微風吹着卷起的紙張,嘆了口氣走近,撿起那兩張紙,拿了個石塊壓着,放在她腳邊。
本來應該離開的。
這時候正是他練劍的時辰。
自他開始修煉之日起,練劍于他而言便如呼吸一般尋常。
無論是在荊棘臺還是青雲天宗,或是山鶴門,他每日都要修煉。
晨起一次,傍晚一次,夜間一次。
一日三次從未有怠。
況且他昨夜送她回來,她卻那般護着淩清虛送她的東西……
他更應該拔腿就走,不再搭理她的。
他低頭瞧向自己的腕上,上頭的一道牙印還十分醒目。
是了,許幻竹還咬了他一口。
時霁凝着眉,神色晦暗,便該讓她就在這躺着。
躺到天黑去。
躺到着了風,受了涼,他也不會再去管她。
但不知怎麽,此刻卻不太能挪的動腳。
他只是突然想起她的一只耳墜子還在自己這裏,現下應該是要還給她的。
如若不然,等許幻竹醒來之後發現自己丢了東西,還不是要使喚他去尋。
反正現在時辰還早,便把耳墜還給她再去修煉也不遲。
這般想着,他幹脆蹲在了竹床邊。
他将懷裏的耳墜掏出來,輕輕挂在她的耳垂上。
白玉墜子随着微風輕搖,瑩潤可愛。
手指離開時,不經意間擦過她的臉頰。
滑滑軟軟的。
甫一觸上,他便立馬抽回了手。
又做賊心虛一般低頭瞧她。
她緊合着雙眼,纖長的睫毛在眼下投下幾道淺淺的影子。
睡得又深又沉。
真是不知道,許幻竹成日裏為何總有這麽多覺睡。
風輕輕吹着,樹影搖曳,他就這麽撐着腦袋看起許幻竹來。
許幻竹的五官細長且骨骼感強,鼻梁很高,顯得有幾分疏離淡漠。
給人的感覺清清冷冷的。
但嘴唇柔軟殷紅,下巴小巧,又添了幾分柔和。
特別是一雙眼睛,笑起來的時候,眼角彎彎,微微下置。
他很喜歡看許幻竹笑起來的樣子。
好像一百只蝴蝶在心底煽動翅膀,風都輕柔起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