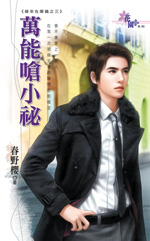慢吞吞的把裘涵安置在沙發上,阿疆轉頭看一眼從辦公室出來的李勁和蔣默安。
見到來人,蔣默安萬年不變的寒冰臉破裂。
阿疆帶着兩分刻意,把裘涵放在沙發上,“深情款款”地對她說:“乖,你在這邊等我,我很快就出來。”
惡寒從心底開起,裘涵肩膀一抖,抖落滿地雞皮。
對,阿疆很壞心,就算裘涵會被Fire也不用怕,他家的公司也很大間。
阿疆大步走到蔣默安面前,比出五根手指,說:“有空嗎?五分鐘?”
蔣默安恢複冷臉,不作反應,他轉身,阿疆立刻跟進去,門關上,那一聲砰!地板微震,很明顯地帶着 怒氣。
阿疆在特特面前沒出息,但在蔣默安面前,出息得很!
這時,被雷轟到的裘涵才想起,自己似乎應該對蔣先生講幾句自清的話,但來不及了,門已經關起。
李勁帶着暧昧笑意,走到沙發邊,“裘秘書想換工作嗎?”
是的話最好,她和方特助就像蔣默安身邊的兩座門神,守得太緊,讓人無機可趁,這對他可不是好事。
裘涵淡淡地搖搖頭,強忍着腳踝的疼痛走回自己的辦公桌前。
她哪有那個膽子,真的坐在沙發上等鄭品疆。
見裘涵不理他,李勁聳聳肩,轉身走掉。
裘涵打開抽屜,翻找出針線盒,蹲到辦公桌下面脫掉裙子,取針穿線,把那道“傷口”縫補起來。
辦公室裏,蔣默安和鄭品疆對峙着,像高手過招似地,仿佛誰先開口誰就輸。
蔣默安望着鄭品疆,還以為那把怒火早就被歲月平息,沒想到,鄭品疆只是出現,沒說話、沒動作,他的火苗立刻茁升轉為燎原大火。
蔣默安不是個情緒輕易外露的男人,但是現在,他有舉槍射人的沖動。
握住筆的手指暗暗用力,青筋浮上手臂,喉結上下滾動,六年前的場景回到腦海中。那年,因為臺風,飛機在臺灣上空盤旋半個多小時才勉強降落。
一顆心像被放在火鍋裏熬,沸騰蒸氣不斷地灼燒,蔣默安反覆地想着,為什麽特特莫名其妙傳來一封分手信,他不知道自己做錯什麽……
不是談過了嗎?他會很忙,她必須諒解,他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她、為了等等。
怎麽可以……短短兩個月,她就投入另一個男人的懷抱,這讓他情何以堪?
他猜那個人是鄭品疆,特特說阿疆是男閨密,他不這麽認為,身為男人對男人的理解,他相信,鄭品疆想做的不止是朋友。
他曾經為這件事對特特生氣,特特解釋,“我和阿疆是姊妹是兄弟,我們是很相像的兩個人,我們都自卑,也都努力從自卑的絕境中跳出來,你給我機會,讓他和我一起改變好嗎?”
她的态度一百分的認真,讓蔣默安無法拒絕。
但真正讓他點頭的是那句——“如果我可以和阿疆成為男女朋友,早在荷爾蒙運作的青春期,我們就會産生關系,以前沒有、未來也不會有。”
她說服了他,可她卻背叛他的信任。
在飛機上,他想出一千種說詞,特特只是在耍脾氣,只是想引起他的注意,只要他好好說,好好說服,特特一定會回心轉意。
他試着把事情往正面的方向想,但是眼見的事實卻把他推進無底深淵。
出了機場,他冒着雨一身濕的招了計程車往特特的住處狂奔。
車子未停,他看見鄭品疆摟着特特上車,她靠在他懷裏,他對她無比親昵,然後……他們一起進了婦産科。
他在婦産科外面等了半個小時,然後……離開。
他不敢再等下去,因為害怕,怕看見兩人臉上的幸福甜蜜。
他想,就這樣吧,終究是因為他離多,是他無法給她依靠,所有的錯通通算在他身上吧,背過身,他拿出電腦上網買了機票。
但他過不了心裏那關,再三的猶豫矛盾,他還是忍不住找上門,他想要求一個清楚明白。沒想到特特不在家裏,沒想到他竟在鄭品疆家中看見穿睡衣的她,并且鄭品疆說,結婚的時候會發帖子給他。
鄭品疆當着他的面把門關上,關掉溝通、解釋,關掉他想說的抱歉。
這次,他真的離開了,一走六年,連回想都害怕。
蔣默安自認是個膽子很大的男人,他勇于冒險、不畏懼向前沖,但是特特讓他害怕,害怕……回首。
那年的八月,他已經不記得自己心裏有多難過,只記得自己像行屍走肉似地上了飛機,記得自己瘋狂工作、瘋狂表現,瘋狂地讓忙碌占滿他神志凊醒的每一秒。
他用整整一年的時間讓自己成功——成功地不讓自己随時随地想到特特,不讓過去的點點滴滴腐蝕心情,他成功地把破碎的心髒縫縫補補,重新擺回正确位置。
他以為若幹年後,再次面對特特,他将會收放自如,像面對商場上的人那樣,表現出友善親和,仿佛他們只是多年失聯的朋友。
他以為自己可以輕易辦到的,沒想到……光是一個鄭品疆,就讓他的以為粉碎。
心裏的火山蠢蠢欲動,他恨不得用熔漿把對方徹底燒熔。
阿疆沒有比蔣默安好到哪裏去,方才逗裘涵的輕松感消失,現在的他像一只蓄勢待發的獅子,準備朝對方狠攻猛擊。
因為特特那句“就算不是蔣默安,也不會是你”徹底惹火他,他沒有辦法把特特抓起來揍一頓,但是對蔣默安……他有什麽好客氣的?
如果每個男人都有自己的拿手武器,那麽阿疆的武器是拳頭,而蔣默安的武器是嘴巴。
蔣默安發出第一波攻擊,他冷笑說:“我還以為鄭先生的辦事效率很高,沒想到都經過六年了,才送來帖子,看來也不過爾爾。”
踏地,火氣從阿疆心底飛竄到腦袋中央!
如果他有帖子可以送,他才不屑跟他動手,他只會居高臨下俯看手下敗将,偏偏他沒有,所以……用力給他……
砰,一拳頭殺過去,即使蔣默安閃得夠快,眼鏡也被他打偏了。
雖然眼眶隐隐作痛,蔣默安卻還是氣定神閑地把眼鏡摘下來,調調鏡腳的角度,重新挂回臉上,慢條斯理地發出第二波攻擊。
“果然是家學淵源,除了拳頭,沒有其他可以拿出手的。”
阿疆再度被激怒,沖到蔣默安身邊,揚起右手。
剛才是猝不及防才挨揍,現在知道阿疆的直線攻擊法,他哪會坐以待斃?
蔣默安快速閃身,這些年的健身房會費不是白繳的,他舉起手臂,及時擋下一拳。
一拳一腳,雖然沒有行雲流水像高手過招那樣,可是兩個長相頂級的男人打架,确實養眼,更何況其中一個還裸着上半身。
阿疆朝蔣默安揮拳,蔣默安險險閃過去了,随手抓起小幾上的花瓶往阿疆砸去。
阿疆像泥鳅似地閃開,他沒有輕功,但腳步輕巧、身形靈活,身上的肌肉随着他的動作,展現完美的線條。
兩人對峙間,蔣默安緊盯着阿疆,扯掉領帶、兩手一拉,襯衫的鈕扣整排掉了。
線條?他也不是蓋的。
蔣默安才把襯衫脫掉,阿疆不給他喘息機會,抓起桌面上的一疊文件往他身上丢,随着紙張擲向對方,他的拳頭跟着進擊。
這一下蔣默安沒躲過,臉頰青掉一塊,但他反應很快,抓起手上的領帶當鞭子使,咻咻咻,順利逼退阿疆。
阿疆觑準時機,用力一扯,把蔣默安的領帶搶過來。
蔣默安單手撐着沙發背,跳到沙發另一面,抓起身後書架上厚重的原文書,一本一本朝阿疆丢,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就在阿疆心裏算着第五本時,出現的竟是蔣默安的拳頭。
他的落點很漂亮,阿疆的嘴角跑出像雲彩般的紫紅色。
阿疆怒吼一聲,也撐過沙發背,抓起對方的書本猛攻。
緊接着,書本落地聲、中拳的悶哼吼叫聲,電話機砸到牆面的铿锵聲不斷出現。
代理董事長辦公室的隔音設備不錯,但裘涵還是聽見一些奇怪的聲音。
身為及格的秘書,她應該立刻撥打分機號碼,或直接進去看看。
可是,她現在沒有裙子可以穿,身上用膠帶捆着一件男性休閑服,外表可笑至極。
如果她想繼續保有這份工作,就不能這樣出現在上司面前,所以在微微的錯愕之後,她低下頭,繼續縫補自己的裙子。
她手腳俐落的縫好裙子,穿回去,剪開膠帶,把男用休閑服脫下來折好。
猶豫片刻後,她泡了兩杯咖啡,以此作為借口,去敲辦公室的門。
沒反應?她悄悄打開一道門縫。
門開,東西落地的聲音清晰可聞,她深吸一口氣,推開門,然後……她要去找大師收驚,不對,要去腦科挂急珍……因為她看到幻影……
搖搖頭、揉揉眼睛,那個是……她家的代理董事長?是她跟了兩年的上司?從來都打扮得一絲不茍的蔣先生現在卻……
辦公室裏一片狼藉,兩個赤裸上半身的男人,各自背靠着一堵牆席地而坐。
很顯然地,兩個人都已經筋疲力竭,只是仍沒有罷手的打算,還時不時抓起腳邊的東西朝對方丢過去。
兩人臉上都帶了傷,赤裸的上身雖然肌肉都漂亮又養眼,但紅紅綠綠的“新式紋身”也精彩絕倫。
照理說,這場架阿疆贏面較大,最後卻打了個平手,他當然不服氣,所以……抓起地上的獎杯,朝蔣默安丢去!
蔣默安不服氣,也随手抓起一本書回砸。
兩個大男人像小孩子似地玩起互丢的游戲。
這是什麽情況?裘涵考慮片刻後,挂起零瑕疵笑容,一如平常般優雅,雖然她的腳踝很痛,還是硬踩着高跟桂走到上司身邊。
“蔣先生,先喝點咖啡。”
蔣默安點點頭,要繼續打架……他需要提神飲料,接過咖啡,仰頭三口喝光。
裘涵走到阿疆身邊,也彎下腰遞上咖啡。“鄭先生,請用咖啡。”
阿疆沒有蔣默安的淡定,在看見裘涵的腳踝時,罪惡感在他心中叫嚣,是他搞出來的!特特交代的事沒做,還弄傷無辜旁人的一只腳……他,腦殘!
他接過咖啡也三口喝光,然後起身。
蔣默安也迅速起身,他以為第二輪正式開打。
沒想到不按牌理出牌的阿疆,竟然一把抱起裘涵,頭也不回地對蔣默安說:“特特想見你,她昨天出車禍,詳情去問章育襄。”
話說完,人也不見蹤影,留下滿臉錯愕的蔣默安,呆愣站在那兒。
他反刍阿疆說的話,三秒鐘後,他快步走到桌邊,拿起電話筒,可惡,電話摔壞了,他翻找着淩亂的桌面,試圖尋找失聯的手機。
找到了,在牆角,不過已經四分五裂,破壞的很徹底。
蔣默安氣急敗壞地用力拉開門,快步走到外面,拿起裘涵桌上的電話,撥出熟悉的號碼。
電話那頭,章育襄剛接起,他便粗聲吼着:“把楊特所有的事通通告訴我!”
蔣默安在醫院碰到帶裘涵看醫生的阿疆。
他們在醫院又打了一架,不過這一架是在男廁打的,因為地方小、又礙于是公共空間,這一架收斂得多。
上一架以肢體動作為主,這一架以言語暴力為主。
“你是人嗎?特特受傷躺在病房裏,你居然帶着別的女人看醫生?”蔣默安怒道。
“我不是人?你才不是人吧!說什麽工作忙,卻是忙着找女人同居。”
“你胡說什麽?!”
“我最好是胡說,要不要談談邱婧珊,談談上流社會婚姻可以替你的前途帶來多少幫助?談談你那個高貴的家世和父母,談談你媽怎麽對待特特?五十萬買斷她的愛情,哼!我都不曉得錢可以這麽用,我想問,下一次你打算擺脫邱婧珊那種上流女人時,得花多少錢?”
連珠炮的話,震呆了蔣默安,原來……這才是特特決定和他分手的原因?
蔣默安不認輸,反口道:“所以你趁虛而入,所以你讓特特懷孕,逼得她不得不和你結婚。”
他的推論讓阿疆錯愕,他居然是這樣子想的?
阿疆很想掐死他。“你在說什麽鬼話!我要是有本事趁虛而入,六年前,我就會把加大版的帖子用空運送到你的辦公桌上,而不是看着特特天天拿着你和邱婧珊的訂婚邀請函大哭。”
“我明明看見你們走進婦産科!”
“蔣默安,你給我聽清楚,特特去婦産科,是要去拿掉你的孩子,聽說他已經有了名字,叫做‘等等’對吧?
“我搞不懂,一個男人怎麽可以這麽沒肩膀,既然沒有本事養孩子,就要有本事不給女人懷孕啊,你要孩子等等,你的下半身就不能等等?
“你媽說,許多狐貍精想母憑子貴、順利上位。真是天大地大的大笑話!蔣家媳婦是行政院長還是總統,有那麽多人搶着做?
“笨特特哭得一把眼淚、一把鼻涕說:‘我不想母憑子貴,我只想留住我的等等。’天吶!原來戀愛真會讓人的智商從人類快速降低成魚類。
“對,是我把她罵醒的,大學沒畢業,打工養活自己已經夠困難,哪有辦法再養一個小孩,我不允許她讓沖動燒壞腦袋。
“是我逼迫她去婦産科拿掉孩子,是我罵醒她,沒有能力的父母對孩子是一場災難,是我咄咄逼人說:‘你自己沒有爸爸,知道沒爸爸的孩子多辛苦,還要讓那個可憐的‘等等’跟你一樣悲哀?’
“我整整罵她一個晚上,她才同意拿掉孩子,可是那之後整整一年,她跟我冷戰。她要死不活,嚴重陷入負面情緒,我知道她恨我,卻又曉得沒有道理恨我,她在心裏不斷拿刀子捅自己,她修理自己、欺負自己,她對‘等等’充滿虧欠,這一切是誰造成的?蔣默安,是你!”
用嘴巴作戰是蔣默安擅長的,但這一架,他慘敗。
帶着一張豬頭臉,口罩和眼鏡全派上用場了,還是掩不住額頭那個腫塊。
阿疆給的訊息讓他花好久時間,才有辦法消化。
怨了那麽多年,氣了那麽多年,可最終他該恨該怨的,竟是自己?
終于站到病房前,蔣默安知道特特就在門後面,只要打開門,就可以看見,可是他……近鄉情怯。
數不清在門前深呼吸過幾次,他始終提不起勇氣敲門,但此時門自動打開了。
那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小女生,很漂亮,很青春。
寧寧長大了,變得完全不一樣,不過越來越像蔓姨,只是那雙眼睛透着靈動、調皮,與蔓姨的沉穩恬靜大不相同。
他去過特特家裏,見過她的家人,特特也想到他家裏見見他的家人,但他沒有同意,因為他的家人……連他自己都不願意面對,怎會希望特特去面對?
可是現在,他終于曉得自己錯得多離譜。
原本不提不說,是希望兩人的感情不受影響,卻沒想到,他的不提不說,竟造成了偌大誤會,造就他們的分手。
寧寧上下打量蔣默安,讀書不靈光,不代表她的腦袋不好用,口罩、眼鏡……他被阿疆哥哥揍了吧?揍得好、揍得解氣。
明明認得,她卻故意裝陌生。“你是蔣默安?”
“對。”他試着讓口氣平穩,但心裏早已驚濤駭浪,翻湧不定。
她指指他的眼鏡、口罩,他順着她的意思拿下來,塞進西裝口袋裏。
他的左眼有一圈黑紫像賤狗,他的右臉微腫,右邊嘴角坯有一塊紫紅色,揚揚眉,寧寧覺得舒服極了。
“你的傷是阿疆哥哥打的?”她明知故問。
“對。”
“身上有沒有?”
蔣默安不知道寧寧問這個做什麽,不過他城實回答,“有。”
她歡快地拍拍手,故意表現親近。“不錯不錯,我就知道我家阿疆哥哥很厲害。”
這話讓他不爽了,我家阿疆哥哥?阿疆哥哥很厲害?不!默安哥哥更厲害,只是厲害在她不知道的地方。
蔣默安的沉穩冷靜在此刻破功,難怪特特總是埋怨妹妹難管教,果然是小屁孩。
“平手。”他冷酷回答。
“平手?說大話!”她輕哼一聲。
“是平手,鄭品疆身上、臉上的傷不會比我少。”他早晚要讓她知道“我家默安哥哥”有多強。
寧寧用鼻孔冷哼一聲。“如果你們兩個登記選姊夫,我會投阿疆哥哥一票。”說完又覺得不夠,補充兩句,“我還會幫阿疆哥哥拉票,把我爸、我媽通通拉過去。”
民主國家、民主時代,二票對一票,姊再喜歡他,都要考慮家人的感受。
蔣默安悄悄地倒抽口氣,話說得這麽明,這年代的孩子都不曉得什麽叫做迂回婉轉,一個個都喜歡單刀直入,又堅持正中靶心嗎?
“鄭品疆的審查資格不符,他無法登記參選。”
既然鄭品疆沒本事空運大紅帖,表示他被特特三振出局,表示他的時機點已經過去,現在開始……對不起,又是蔣默安的時代。
“哈哈!那你曉不曉得,早在六年前,你的資格就被注銷了。”寧寧瞪眼。
再次正中靶心,和小屁孩對壘,心髒不夠好的很容易暴斃。
他正想找點什麽話,好閃過小屁孩直接進病房,這時,門後多了張臉,那是李蔓君,特特常說的——像白雪公主的媽媽。
“蔓姨,好久不見。”
李蔓君拍拍寧寧的背,寧寧讓開一步,她站到蔣默安面前說話。
“特特想見你,不過傷口太痛,我們請護理師幫她打了藥,剛剛睡着了,你要不要先回去,晚一點再……”
“不,我進去等她醒來。”
李蔓君想了想,點點頭說:“那特特就麻煩你照顧,寧寧,你不是想去看爸爸嗎?章律師打電話過來,說爸爸那邊沒有人。”
聽見這話,寧寧用力點頭。
太好了,為了姊姊和阿疆哥哥的計劃,她和媽媽必須詐死,幸好這間醫院是她爸爸投資的,而且姊姊是用假名住院,她們還活着的事被封鎖住,但也因此她們不能到處亂晃,成天待在病房裏,她都快發黴了。
哄走寧寧,離開前,李蔓君把自己的手機號碼給了蔣默安。“這是我的電話,如果蔣先生要回去,麻煩告訴我一聲,特特現在離不開人。”
“好。”點點頭,他說:“如果蔓姨不介意的話,請喊我默安。”
李蔓君來不及回答,寧寧便将她給拉走了,還轉身朝他皺皺鼻子說:“對不起,我媽很介意!”
蔣默安搖搖頭,轉身走進病房。
看到特特那一刻,像是電流竄過全身,心悸、顫栗、疼痛……無數的情緒在腦海裏喧嚣呼嘯,他無法思考,眼裏心裏腦海裏裝的全是她。
二十歲的特特、像兔子般的特特、烤蛋糕的特特,自卑又自傲的特特。
他曾問過她,“這麽自卑的你,為什麽敢向我告白?”
她說:“我想把自卑驅逐出境,讓一個明星級學長愛上我,是最簡單的捷徑。”
他回答,“在我面前,你不需要敢上驕傲面具,想自卑就自卑,有我擔着。”
他很清楚,驕傲只是她的面具、不是她的本性,他願意縱容她的自卑,也不肯她壓抑。因此,此時此刻,他分外痛恨自己!
明明知道驕傲只是她的面具,并非本性,為什麽在她提出分手時,沒有去深究背後原因,他怎麽可以讓一場誤會斷了兩人之間的情分?
他很清楚,她是那樣地深愛他、離不開他,這樣的她,怎麽可能在短短的兩個月內移情別戀?
是他的錯,如果他肯開誠布公,告訴她,自己和那個了不起的家族有多麽格格不入,如果他早點告訴她,他做的每件事,背後目的都是想和家族切割,她便不會産生誤會。
他不想當醫生,他想向全世界證明,考不上醫學院的孩子,不代表不優秀。
他和特特不同,他是真真切切的驕傲,即使是在父母長輩面前,他也要獨占鏊頭。
所以他渴望成功,他要揚眉吐氣,把在外人面前的驕傲晾在家族長輩面前。
應該早點告訴她的,可是他從來不說……
緩緩吐氣,手指輕輕滑過她的臉龐,特特長大了,臉上已不見當年的稚嫩青澀,這些年,她吃了多少苦頭?
剛才從章育襄嘴裏曉得特特的身份,太吓人了!
他沒想到特特竟是董事長的女兒,如果早在六年前知道,他是不是就可以說服她、把她帶在身邊,給她一個截然不同的生活?是不是就可以讓他們的“等等”不必再“等等”?
心隐隐抽痛,那年,他到底做過多少蠢事?
“對不起。”他低聲在她耳畔說。
特特始終沉睡,他始終看着她的容顏,仿佛要把錯過的這幾年通通補回來。
特特離開後,他再沒有談過戀愛,喜歡他的女人不會比學生時期少,告白的人數會讓人瞠目結舌。
特特說過“你有一雙桃花眼,凡是女人都逃不過”,但他很凊楚,這輩子再不會喜歡一個女生像喜歡特特那樣,所以他戴上眼鏡,遮掩自己的桃花,所以他養兩只兔子,看着它們想着特特。
他也不知道特特到底哪裏特殊,只是……除了她,他的心再不為誰萌動。
握住她的手,他下定決心,在她耳畔低聲說:“我們從頭來過吧!”俯下身,他親親她的嘴唇,鄭重道:“這次,我們一定會幸福。”
現在的他,有足夠的能力為她圓起夢想,現在的他負擔得起很多個“等等”,也負擔得起婚姻家庭,現在的他,再不害怕做出的承諾無法兌現。
病房門被打開,進來的不是醫護人員,是章育襄。
“你的手機呢?我打那麽多通電話,你怎麽不接?要不是蔓姨說你在這裏……”話說一半,他才發現蔣默安臉上的精彩,不會吧……“你打架了?”
“對,打架了。”
“為誰?”
他轉頭,看一眼床上的特特,笑得滿臉溫柔。
哇咧,天要下紅雨了,就在百分之八十的人認定他是同性戀之後,他居然對董事長的女兒……一見鐘情?這個楊特是怎麽辦到的?
一把将蔣默安抓到牆邊,章育襄低聲道:“喂,你不會是以為董事長身體不行了,想要勾引楊特,名正言順拿到經營權吧?”
蔣默安失笑,六年前特特被母親指控妄想高攀,六年後輪到他被指控,果真是風水輪流轉啊。
“容我提醒,不需要勾引特特,我現在已經拿到公司的經營權。”
“你只是代理董事長,不是真的董事長,別以為這樣就可以篡位。”章育襄正經回嘴。
“你怎麽确定我是篡位,不是董事長想要傳位?”
“我告訴你哦,你不可以做過分的事,董事長對我們有恩。”
“這件事,我比你更凊楚。”蔣默安橫他一眼,一不小心視線掃過,又定在特特身上,挪移不去。
章育襄發覺,刻意挪動腳步,擋住蔣默安的視線,一副保護者姿态。“不準你動楊特的歪腦筋。”
沒有保護好她,讓她受這麽大的傷害,章育襄面對董事長,已經罪惡感重到快擡不起頭,要是楊特再被蔣默安……
蔣默安與章育襄對上眼,思索片刻後,冷靜問:“你喜歡特特?”
喜歡特特?
不,他是視覺型男人,如果姊妹倆非要他選一個,他怎樣都會選楊寧。
不對不對,董事長鄭重地把蔓姨和一雙女兒托付給他,他怎麽能監守自盜?
“我喜歡的女人多了,但不管喜歡誰,都不會把身家條件當成重點。蔣默安,你不要把自己的前途押在楊特身上,我不會同意的。”
“我不需要你的同意。”
繞過章育襄,他重新走回床邊,重新把目光定在特特臉上,他對她百看不厭,是很多年前就有的自覺。
他的專注度很高,看書的時候,任何聲音影像都不會影響到他,可她在小小的套房裏烤餅幹、燙衣服、擦地板……他的視線總會不自覺被勾引,她是破壞他專注度的超級病毒,而他,心甘情願為她中毒。
“默安……”章育襄試圖阻止,卻被蔣默安的下一句話打斷。
“特特是我的初戀,一場誤會造成我們分手,老天再次把她送到我身邊,這次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放手!”說這些話的時候,他連一眼都沒有看章育襄。
章育襄被定身,天底下有這麽巧的事?
對啊,如果不是這麽巧,蔣默安怎麽會突然打電話問他關于楊特的事?
他又不曉得自己偷偷聯絡上蔓姨,不曉得她們母女在上海,現在的他,應該待在辦公室裏,對付那群痛恨他接棒的老狐貍。
他是個律師,邏輯、分析是專長,短短幾秒鐘內,他串起前因後果。
“這件事,董事長知道嗎?”
“蔓姨大概會對董事長說吧。”
點點頭,章育襄再度把他拉到一旁,蔣默安臉上帶着濃濃的不耐煩。
他的表情讓人冒出大大小小的雞皮疙瘩,章育襄心底響起警訊,不會是打架打上瘾了吧?
章育襄在他想揍人之前,飛快把話說清楚,“既然是你前女友,這件事你幫忙承擔吧!”
“什麽事?”
“昨天的車禍不是意外,是預謀殺人。”
預謀殺人?蔣默安臉色瞬間變得鐵青,目光淩厲,章育襄毫不懷疑,他的暴力因子徹底被激發。
“說清楚!”
“昨天,蔓姨和特特、寧寧搭着鄭品疆的車子回飯店,那裏有鄭品疆的人接應,本想着不會有問題,沒想到一部失速的車子沖過來。
“特特推開蔓姨和寧寧,自己卻躲不開。她的右腿骨折,輕微腦震蕩,幸好沒有內出血,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“鄭品疆的人把肇事者抓住,交給公安,後來我接到鄭品疆的電話,他告訴我,不是意外,是謀殺,他讓我對外放出假消息,說出蔓姨母女三人都死于這場車禍事故。”
“他為什麽要這麽做?他有什麽證據證明這是謀殺?”
“我要是知道就好。不過我透過關系,參與整個審訊過程,居然被鄭品疆說中了,果然是預謀犯罪,只不過他的目标是蔓姨,他收下指使者三十萬人民幣。”
“他有沒有說出誰是主使?”
“他不知道姓名,他們約在飯店房間裏見面,見面時對方戴了面具,坐在椅子上,長相身高都不确定,只确定是個男人,中等身材,穿窄管貼身七分褲、白色運動鞋,手上戴着金表。”
“肇事者人呢?”
“收押了,事關‘三條人命’,他不能見客。”換句話說,幕後指使者也見不到他。“我剛去查他的存款記錄,當中并沒有這筆錢,他說必須等到消息發布之後,錢才會彙進來,我剛動用人脈去電視臺,明天将會發布這則新聞。”
“董事長怎麽說?”
“董事長在生病,這件事還不敢讓他知道。”希望楊寧那個笨小孩不要說漏嘴才好。
“知道了,手機給我。”
章育襄沒有多想,把手機交給他,蔣默安撥下一串數字,電話那頭飛快接起。
“蔣先生您好。”方特助的聲音。
“還在外面?”
“我在計程車上,快回到公司了,億翔那裏沒問題,約定後天簽約。”
“你把辦公室裏的文件送到XX醫院516病房,我的手機和電腦摔壞了,在辦公室的地板上,你找一找,再幫我買新手機和電腦送過來。”
“是。”
方特助雖然不明白為何手機電腦會摔壞,但他已經習慣使命必達,應下話後,他讓司機加快車速。
“需要多久時間?”蔣默安問。
方特助看一眼手表,心裏默算之後回答,“兩個小時之內。”
“好,我等你。”
只是,當方特助回到公司,打開董事長辦公室門時,看見滿屋子的淩亂不禁呆住了,這是恐怖組織入侵嗎?強烈驚吓後,他飛快地找手機電腦,但滿地的文件……天,兩個鐘頭哪夠?他苦着臉,抓抓滿頭亂發。
章育襄皺皺眉頭,蔣默安要在這裏辦公?
不過那是他的人身自由,他管不得。“我有幾個疑點,但鄭品疆不知道跑到哪裏,我沒辦法問。”
“什麽疑點?”
“第一,楊特和鄭品疆好像早就知道會發生意外,鄭品疆甚至從臺灣帶來四個身手不錯的兄弟。”如果不是他們,肇事者早就駕車逃逸,他們是從哪裏知道,有人将會對蔓姨不利?
“也許只是為了以防萬一。”
蔣默安嘴巴這樣說,心裏卻不完全同意,特特不喜歡麻煩別人,這樣大張旗鼓地出現,必有其原因。
“事情發生後,鄭品疆的處理方式太奇怪,我不懂,為什麽要謊報三人的死亡?但他一味堅持,蔓姨和寧寧雖然不知道為什麽,卻支持他的決定,從鄭品疆透露出來的話中,這個決定出自特特。”他看一眼特特,她微皺眉頭,似乎睡得不安寧。
“等特特醒來,我再問她。”蔣默安說。
“好,那我先過去董事長那邊。”
“嗯。”蔣默安應聲,章育襄轉身,這時床上傳來動靜,兩個人同時回頭,特特醒了。
特特張開眼睛,蔣默安出現眼前,她靜靜地望着他,又來了,每次心慌意亂、處境窘迫時,就會作有他在身邊的夢,這個習慣實在不太妙。
緩緩閉上眼睛,仿佛她又看到坐在書桌前的蔣默安,她靠近,他便擡頭對她微笑,沒說話,一個微笑就讓她的腦袋吞下大量迷幻藥。
她看見幫自己挑衣服的默安,他沒什麽錢,卻是一攢夠錢,就慷慨大方地給她買洋裝,讓很久很久沒當公主的她,重新當回公主。
每次出門前,他喜歡給她挑選衣服,他堅持兩人穿情侶裝出門,他說:“我喜歡你身上貼着‘蔣默安專屬’的标簽。”
她看見站在廚房前,蔣默安高瘦的背影,月歷上有一排紅色的圈圈,那是她的生理期,他老在她的生理期之前,細心檢查抽屜裏從十三到三十二公分的衛生棉尺寸齊不齊,櫃子裏的紅豆、巧克力,需不需要補貨。
他對她的寵,在每一個微小的地方,讓她随時随地感受得到。
這樣的行為……誰會不相信他待自己是真心實意?
她應該對他生氣、怨怼的,但那些微甜的記憶,一堆一堆地塞滿胸口,數量太多,多到她裝不下負面情緒,多到她無法遺忘他,多到……兩千多個日子過去,她依然想他。
怎麽辦呢,念念不忘一個已經分手的男人,她如何讓自己的感情路繼續往前走?
“唉,我還以為醒了。”
是章育襄的聲音,緊接着……一聲熟悉的嘆息,她一個激靈,整個人迅速清醒,張開眼看向臉上青青紫紫,像被刑求過似的蔣默安。
真的是他!不是夢境……
“她真的醒了!”章育襄說。
“有沒有哪裏不舒服?”蔣默安急忙問。他摸摸她的手、摸摸她的頭,又說:“醫生說你有腦震蕩現象,需要再觀察,你會不會覺得惡心?想不想吐?”
他的體貼一如多年前,好像兩人之間沒有分手這件事,他怎麽可以這樣自然?
她皺起眉,深吸氣……她想起來了,是她想見他,是她讓阿疆找他,所以他和阿疆……打架了?以己之長、攻彼之短,阿疆真聰明,可他也真笨,為什麽不閃!
不自覺地,心疼浮上眼簾。
看見她的眼神,蔣默安的心情無比暢快,她還在乎他、心疼他?快樂在他臉上現形,讓他已經夠精彩的臉變得更精彩。
害怕自己受他影響,特特別開目光,對上章育襄,口氣刻意清冷。“我有很重要的話要說。”
“好,不急,我先幫你把床搖起來,會痛的話,要告訴我。”
蔣默安搖起病床,在她背後墊枕頭,然後幫她倒杯水,把冷氣的溫度往下調,檢查點滴有沒有正常……
蔣默安和楊特的反應兩極化,一個熱烈、一個冷淡,顯然兩人心裏想的、要的不一樣,莫非是當年的分手,某人處理得非常糟。
勾勾唇,帶着看好戲的心情,章育襄坐到特特正前方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