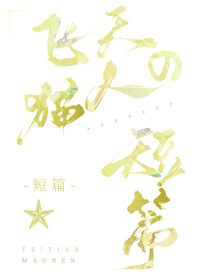從前柳山齋的師傅還在時,山鶴門一共有三間閣樓,七八個大院子,還有一塊練劍用的場地。後來門中的人漸漸少了,地也被青雲天宗回收去養了靈草。
許幻竹帶着時霁停在山鶴門的大牌匾前,“鶴”字的左邊褪了顏色,只剩一個“鳥”字。
她有些尴尬地笑了笑:“我和掌門都不是重物欲的人,過得比較簡單質樸,你剛來可能不适應,習慣幾天就好了。”
時霁盯着那牌匾,狀似無意道:“師尊似乎與掌門很是相熟,莫非師尊來山鶴門之前便與掌門相識?”
許幻竹其實不大樂意與人講以前的事。她怕同時霁說她與柳山齋早早就認識之後,他又要問他們是怎麽認識的,或是她為何來山鶴門。
于是信口胡謅了句:“我和他從前不認識,後來我來了山鶴門之後才慢慢熟了起來。”
她這般說完,時霁果然沒有再問什麽,只是點頭跟着許幻竹進了她住的院子。
院子不大,只有四間木屋子,正中的場地上種着一棵桃樹,樹上結了些桃子,壓着桃枝往下墜。樹下是一架竹床,地上圍着竹床種了許多月季,這個時節開得正熱鬧。
許幻竹門口的檐梁下挂着一只鳥籠,裏頭住着只翠色的鹦鹉,兩人一進門就不停地叫着“許幻竹、許幻竹”。
“翠翠,餓了吧。”許幻竹朝着鹦鹉擡了擡下巴。
“時霁,你随便看看,你可還滿意?”
我就是随口一問,不滿意也沒辦法。
許幻竹腳步往前,裙衫飄飄,顯然沒打算等他的回話。
“多謝師尊,這裏挺好的,我很喜歡。”
時霁跟在她身後,看着她抓了一把谷子,撒在鳥籠裏。
翠翠低着頭一戳一停地吃起來。
許幻竹拍了拍手,一邊往屋裏走,一邊往前指了指,“你喜歡就好,你就住我對面那間屋子。今日忙了一天,收拾收拾去休息吧。
我也去睡一會,有事就叫我”,她将門推到一半,又停下糾正自己,“有事也不要叫我,自己看着辦。”
說罷,“吱呀”一聲,房門被合上。
十分幹脆。
時霁擡頭看了看天色,夕陽晚照,落日餘晖,照得整個院子暖融融的。花草樹木随風微搖,站在這裏,好像能暫時洗滌掉疲累,人都松快下來。
他伸手将鳥籠邊上的一顆谷子推進去,透過鳥籠子的空隙往裏望去。
許幻竹的作息,還真是健康。
小院的日光往後一寸寸偏移着,夜幕籠上屋檐。
屋外有風漏進來,許幻竹緊了緊被子。
真奇怪,她明明記得進來之前把門關好了的。
又是一道冷風,直直迎着面門劈過來。房門大開,門扇四下晃蕩。
許幻竹‘騰’地一下坐起,抓起桌上的長劍閃身躍入了小院。
剛站定,一道劍鋒閃着寒光,從耳側刺穿氣流,橫撲而來。許幻竹舉劍去擋,哐哐當當的劍器相撞的聲音在小院裏響起。
“師尊,弟子鑽研了一下午,有幾招劍式不太明白。”
時霁的劍招,野蠻沖撞,帶着年輕人身上特有的血氣方剛的莽勁兒。
許幻竹生平,最恨人擾她睡覺。幾個招式對下來,她已然從防守狀打成了進攻狀。
又是一劍,時霁往後退了一步,一腳踩中了牆下新開的一株月季。月季被他一腳踩得按在地上,許幻竹臉色不太好,他見狀飛快松開了腳。
“師尊抱歉,弟子不是故意的。”
踩她的花?
許幻竹眉頭一跳,這倒黴徒弟,這才剛來,就屢屢觸她眉頭,非得給他點顏色瞧瞧。
她後退半步,斜着身子,劍尖點地,橫空轉了半圈,借力猛地刺了過來。
時霁怕再踩到院子裏的花,這一回沒敢放開了接,連連躲避退閃,幾個來回的功夫便被許幻竹壓在了牆角,“你出招太浮躁,心不靜,意不純,劍不精。好好練練心法吧。”
許幻竹半張臉隐在夜色裏,離得近了,只看見她一對唇瓣上下翕動,她一字一句地警告:“還有,下次不要在我院子裏練劍。我睡覺的時候,也不要叫我。”
剛打了一場,兩人都微微喘着氣,時霁被許幻竹一把劍壓着,渾身不自在,微微往後錯開了些距離,耳尖微紅,順斂着眉眼回道:“師尊教訓的是,弟子知道了。”
認錯的态度還算良好,許幻竹收回手來,正要離開,卻突然感覺胸中一悶,腦袋發昏,直直往後栽去。
時霁甩了劍伸手去接,手還未碰到她,後頭突然冒出個青衫男子,一把将許幻竹攬住。
“去将她房裏櫃子上的白色藥瓶拿來。”
那人說話時冷靜沉穩,波瀾不驚,倒是和俊逸風流的外表有些出入。
時霁收回打量的目光,點了點頭就去房裏拿藥。
柳山齋扶着許幻竹在樹下的竹床上坐下,許幻竹緩了口氣後在後頭添了一句:“時霁,桌上的酒也拿來。”
時霁腳步一頓,一瞬間覺得今日自己對許幻竹的試探有些多餘。
懶怠、嗜酒、不求上進。
這人似乎和傳聞中沒什麽差別。
許幻竹吃了藥,才終于順過一口氣來,又舉着酒瓶子仰頭灌了一口,胸口那股滞澀酸脹也被帶下去不少。
“說說吧,你今日又幹什麽了?”柳山齋拿過她手裏的酒瓶,擺到一邊。
“我徒弟”,許幻竹指了指站在一邊的時霁,“非要我給他指點劍法,一下沒注意,就這樣了。”
說完,許幻竹又去撈一邊的酒瓶,柳山齋見狀幹脆拿着酒瓶站了起來,走到時霁面前,笑得十分慈祥:“這就是今日青雲山上拿了第一的那個孩子吧。怎麽想要來我們山鶴門的?”
許幻竹見狀也撐着腦袋,好整以暇地看向時霁。
翠色的袖子垂下一截來,堆在肘間,露出一段白如新雪的手臂。
時霁不着痕跡地移開視線,從袖中摸出一個玉色的藥瓶,藥瓶的底端寫着個‘柳’字,他将那一頭對着柳山齋,遞了過去,“十年前,在留仙坡,多謝前輩贈藥之情,時霁一直銘記于心。”
山鶴門一窮二白,柳掌門把門中所有財産都刻上了字,這樣萬一丢了還能找回來。
這個事情,整個修真界都知道。
柳山齋拿着那藥瓶子,在手中轉着看了半晌,才恍然大悟,挑眉看向許幻竹。
許幻竹聳了聳肩,偏過頭去開始理腰帶上的褶皺。
柳山齋笑呵呵地将藥瓶遞還給時霁:“舉手之勞,不足挂齒。”
“許仙長,外頭有人找。”看門的小童雙雙從院門探出頭來。
“誰啊?”許幻竹下了竹床,往外走。
雙雙往後退了半步,指着大門口的人影道:“一個穿藍衣的道長,長得很好看,不過不太愛說話的樣子。”
“我出去看看。”許幻竹對着兩人喊了一聲,便攬着雙雙的肩膀一道往外走了。
許幻竹來了山鶴門十來年,除了去青雲山就沒出過門,還能有誰找她?
柳山齋也想跟出去看看,但顧及時霁在這,于是故作正經地提醒了幾句:“你師尊有舊傷,修煉上不懂的,以後讓她口頭上指點你就行,不要勞煩她動手。還有那酒,你看着她些,不要讓她多喝,她身體一難受啊,不愛吃藥,就喜歡用酒來麻痹自己。可這酒喝多了也傷身啊,哪能像她這般當做水喝。”
時霁望向竹床上的白瓷酒瓶,不知怎麽想起方才許幻竹舉瓶豪飲的樣子。
她那時急急從他手中将酒瓶拿去,仰頭喝下一口,透亮的酒水順着唇角流下來,淌了幾滴到她的衣襟上。
他只道她是個急酒之人,如今看來,當時自己害得她舊傷複發,她應當是十分難受。
像她這個年紀的姑娘,若是磕着碰着傷着了,巴不得把傷口揚着,告訴全天下,好叫所有人都對其噓寒問暖,關懷備至。
許幻竹倒好,寧願叫人以為她是個急好酒色,不求上進的懶怠之徒,也要将傷口捂着、藏着。
他突然有些好奇,許幻竹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?
時霁将視線收回,點頭道是,又看向柳山齋的腰間。
那一處空蕩蕩,什麽東西也沒有。
“弟子見青雲天宗的人都愛佩玉,不過師尊和掌門好像沒有這個習慣。”
柳山齋望着門口,答了他一句:“我從不戴這些,你師尊從前倒是戴,如今也不戴了。時候不早了,我也不打擾你了,你早些休息。”
時霁點點頭,柳山齋便也離開了院子。
望着柳山齋離開的背影,時霁眉心動了動,一雙眼睛忽地暗下來。
那人不是柳山齋,但他方才說答謝之時,柳山齋确然已經應下了,可見真正救他的人與柳山齋相識,且不願透露自己的身份。
時霁将目光投像牆角,那株紅色的月季撲到在地,随風瑟縮。
難道是許幻竹?
可許幻竹分明說,她是來了山鶴門之後才與柳山齋相識的,而許幻竹到山鶴門的日子,是在他去荊棘臺的第二日……
許幻竹今日曾問他,為何來山鶴門,他說是為了那份恩情。那時的許幻竹,情緒好像也未見幾分波瀾。時霁走到牆角,将那株倒了的月季扶起加固。
反正,還恩情的說辭,是講給許幻竹和柳山齋聽的,若是實在找不到那人,那便算了吧……
月光打在花枝上,兩只修長的手指細細摩挲着深綠色的葉片。
月色中有人輕嘆。
柳山齋走後,時霁沿着小路去了大門。
于是遠遠看見山鶴門牌匾下面的景象,一男一女,藍衫綠影。
正是許幻竹和……淩清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