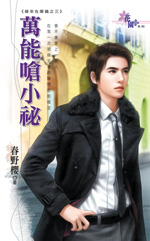櫃子倒地後發出了一聲巨響, 那聲音透過木板傳上來,震得人頭皮發麻。
床榻那一邊突然停了動作,秋書榕的聲音傳了出來:“什麽聲音?”
許幻竹吓得一頭栽在時霁懷裏, 屏氣凝神,不敢動作。
陳坡下了床, 繞過屏風往這邊看了一眼,接着又回了床榻上, 只聽到他滿不在意地對秋書榕道:“倒了個櫃子, 不必大驚小怪的。”
那兩人倒也真沒放在心上, 轉頭又繼續辦起事兒來了。
床架子又開始被撞得吱呀亂顫。
許幻竹這才稍稍松了口氣。
“師尊, 你沒事吧?”頭頂上傳來時霁的聲音。
這語氣聽着竟還十分磊落大方,好似絲毫沒把剛剛自己做的混賬事放在心上。
他一雙手輕輕攏在許幻竹肩頭, 而許幻竹因為整個人靠在他懷裏, 他說話時, 胸腔帶起的震動透過衣料傳到她耳邊, 聽起來格外清晰。
她忽然有些氣悶, 于是摸着黑從時霁身上半撐着起來, 試圖讓自己的身體與他隔開一些距離,接着壓低了聲音質問道:“你方才為何親我!”
“可方才我若不那樣做,只怕師尊早就被當成賊人捉起來了。”
他這一副理所當然的模樣看的許幻竹想給他一拳。
“你可以捂住我的嘴, 或是将我打暈,不必非得……”
兩人說話間外頭還配着床架子的吱呀聲和細細密密的喘氣聲,許幻竹從來沒覺得像現在這麽尴尬過,‘親我’兩個極簡單的字梗在喉嚨裏,不上不下。
“非得什麽?”他往上擡了擡下巴, 語調輕緩,一句話問得缱绻旖旎, 引人遐思。
許幻竹覺得,時霁這一張嘴,有時候真的是十分讨嫌。
等日後出去了,她非得找個什麽高級些的禁言術法,叫他一天到晚沒點眼力見兒。
“懶得理你!”許幻竹撇過頭去,不願再與他多話。
只是她這個動作實在有些累人,全身的力氣壓在兩只胳膊上,沒一會兒,她便開始覺得有些麻了。
又再堅持了一小會兒,她漸漸有些體力不支,頭腦發昏,再加上櫃子裏的空氣本就密閉,于是更覺得氣悶。
此時,外頭兩人好似消停了些,她聽見他們又開始說起話來。
“榕兒,明日戌時我便要走了,咱們明日再見一面吧。”
“今夜這一夜你還不夠麽,再說了明日白日裏我是不可能帶你進來的。”
“與榕兒在一塊,一百日,一千日我都不嫌多的!大不了明日我不來府裏,我們去老地方碰面可好。
況且我這一趟去了不知要什麽時候才能再出來,你可心疼心疼我吧。榕兒,我的好榕兒。”
“行了行了,明日我再去見你一面總成了吧。”
“成!”
‘啪嗒’,一滴汗順着許幻竹的臉頰緩緩地滴下,落到了時霁頸窩裏。
他終是看不過眼,伸出雙手扣在許幻竹的腰上,稍稍用力往前一帶,許幻竹腰下一塌,整個人自然而然的又落回了他懷裏。
她很是抗拒地掙紮了一番,時霁将她按住,附在她耳邊輕輕說:“師尊平日裏,除了吃就是睡,這會兒能堅持這麽久,已經很不錯了。”
在許幻竹氣得跳腳之前,他又指了指外邊,繼續道:“再說了,還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出去呢,師尊不如安心休息一會兒。”
算了,算了。
許幻竹深吸兩口氣,她這雙手實在酸得很,懶得與他争口舌之快了。
再說了,在時霁面前,她好像也沒什麽形象和面子可言。
想通了這一點,她一腦袋紮了下去,像鴕鳥一樣,再也沒起來。
只是眼睛一閉上,腦子裏浮現出方才那個極其荒唐的吻。
唇瓣相交,厮磨缱绻之際還叫她發現,那家夥的嘴唇其實還挺軟的……
不過想她許幻竹這一輩子,一直潔身自好,從不招惹是非,在收這個時霁徒弟之前,更是連男修的小手都沒拉過。
如今給他當了個勞什子師尊,那是抱也抱了,小手也牽了,小嘴也親了。
放眼整個修真界,像她這麽言傳身教帶徒弟的,那還是頭一個。
越想越虧是怎麽回事?
一片黑暗中,時霁的唇角不受控制地微微勾起,一只手從她腰間緩緩收回,落到自己的嘴唇上,輕輕點着,似是在回味。
接着又慢慢攏上她的頭頂,隔着些距離,像是在仔細勾勒她的輪廓。
他一時愧于方才那個吻 ,實在趁人之危,一時又懷念唇畔柔軟的觸感,開始後悔沒能親久一些。
是以當許幻竹均勻的呼吸聲噴灑在耳邊時,他心底裏忽然蔓生出個極荒唐的念頭。
這一刻覺得,就這麽與她在這裏呆着,一直呆着,好像也不錯。
後半夜,床上那兩人終于入了睡,時霁和許幻竹從櫃子裏偷偷出來時,已是寅時了。
回去的路上,許幻竹踢着石子兒,走在前邊。
時霁一言不發地跟在她後頭。
“時霁,陳坡方才說,今日幾時要離開來着?”
“戌時。”
“那我午後便來這守着,等着一會天亮了,路好走些的時候,你就去浦荥山找田清榮,想辦法把他騙下來。”
“好。”
兩人繼續往前走了幾步,許幻竹又停住,看了時霁一眼,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。
“師尊還有什麽要交代?”
“就是方才……在櫃子裏的事情,能不能當做沒發生過?”
許幻竹難得局促,這一句話說出來,怕是也做了不小的心理鬥争。
時霁往前錯開一步,微風揚起他一小塊衣角,只給許幻竹留下個背影,他幹脆利落地拒絕道:“不行。”
“不行?”
這逆徒在說什麽?
許幻竹大驚,兩步追上他,一把拉住他的袖子,“為何不行?”
“弟子從未親過別的姑娘,今日若不是為了助師尊不露馬腳,弟子也不必出此下策,無端失了清白。”
“你師尊我也沒被別人親過啊!我也失了清白啊!所以呢?”許幻竹拉着他袖子的手受了莫大的刺激,直接抓着他的兩只胳膊質問道。
“可弟子不像師尊那般沒心沒肺,所以沒辦法當做無事發生。”時霁輕輕拂開她的手,說得十分認真。
“我……”許幻竹被他推開的一雙手停在空中,緊握成拳。
她沒心沒肺?
很好。
許幻竹閉上眼深吸了一口氣,咬牙切齒地開口:“你想怎麽樣?”
“要麽,師尊直接對弟子負責”,他朝她走近一步,眉骨上打上點月色銀霜,無端露出股十分危險的氣質。
也是,他其實從來就不是什麽聽話的小羔羊,而是只披着羊皮的豺狼,只不過一貫掩飾得比較好,倒是險些叫她忘了他本來的樣子。
于是許幻竹跟着他的動作也後退一步,伸手隔開他要繼續往前的步子,“請你直接說第二個‘要麽’。”
“要麽,師尊答應弟子三個條件,若是師尊做到了,弟子便如師尊所願,忘了今日發生的一切。”
許幻竹飛快應下:“好,我答應你。”
小兔崽子,什麽三個條件,還想威脅你師尊。
等明日戳穿了那陳、秋二人,找回那幾個倒黴蛋,出了這陽襄村,姑奶奶就不陪你玩了!
本來還想掙點靈石再跑路,如今看來,還是得早點離開山鶴門這個壓榨她十年的美好年華的地方,離眼前這個瘟神離得遠遠的!
離開這裏之後,她便去找個沒人知道的地方,帶上翠翠,辟一間小屋子,種滿花樹,夏時在樹下乘涼聽蟬,冬日在樹下溫酒賞雪,真是美滋滋。
光是這麽想着,許幻竹已然有些飄了,臉上的笑意也盛不住,落在時霁眼裏,只覺得十分詭異。
“弟子還沒說是哪三個條件。”
“你說什麽我都答應你!”許幻竹拍拍他的肩,心情頗好:“天亮之後還有好些事要做呢,我們快些回去休息一會。”
時霁被她拉着往回走時,心裏只有一個念頭:許幻竹不對勁。
鬼知道她又在琢磨什麽。
可腳下卻不受控制,一步一步的,十分聽話地跟在她後面。
夜色溫柔,拉着兩人的影子,投射在田埂上,小路上。
時霁看着許幻竹的側臉,微風吹起她鬓邊的幾縷青絲,露出她尖尖小小的下巴,瑩潤的耳垂,甚至帶着股若有若無的幽香傳到他鼻尖。
他心底突然軟下來,其實陽襄村也沒什麽不好的,這裏與世無争,沒人認識他們,沒人打擾他們。
若是,再遲一點找到那幾人就好了。
他大概是太貪心了。
私心裏企盼着,和許幻竹扮演夫妻的這段日子,再長一點就好了。
這夜,這月色,再長一些,就好了。
淩虛宗通往主殿的百餘級臺階頂端,是賞月的好去處。
站在那高階上,仿佛一伸手,就能碰到月亮。
淩清虛腰間的長劍在月色下閃着瑩瑩冷光。他一只手流連在冰涼的劍柄上,劍柄上的花紋厚潤,就這麽輕輕觸着,好似就能叫人靜下心來。
他擡眼往天上看去,不知許幻竹在泗陽,過得怎麽樣了。
她手下那幾個男弟子,都不是什麽省心的,也不知她是否應付得過來。
還有那個人,那個日日跟在她身側的人。
他捏緊了劍柄,手背上的青筋泛起,透露出幾分猙獰的意味。
十年前的事情那樣慘烈,他從荊棘臺出來,又故意接近許幻竹,究竟有什麽目的?
既是罪人之後,茍延殘喘至今,心中所圖所謀必然也是些見不得光的東西。
這樣的人,絕不能留在她身邊。
也許這一次去泗陽,正是個好機會。
君沉碧第一次見到淩清虛臉上露出那樣的情緒。
冰冷、陌生、叫人從心底無端生起冷意。
她收起從君雲淮那裏拿來的宗門事務清單,眼中忽然明朗,她就說,淩清虛為何會把這些東西交給君雲淮?
看來,他是準備要去找許幻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