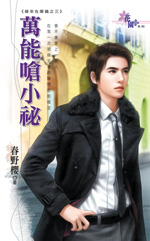梅問情那頭喝茶聊天,由慧則言菩薩敘述往事,雖說也能夠慢慢地讓梅問情有個印象、逐漸想起來,但畢竟沒有那麽強烈的沖擊力。
到了另一頭賀離恨這裏,他的意識仍舊沉浸在記錄畫面當中。
兩人雖然因意外釀成了那種局面,然而穿上衣服時,賀離恨仍舊是個無情冷酷的修行者,一邊離不了她,一邊卻又睜眼說瞎話,跟她劃清界限身份。因為他這張床上床下兩套說辭的嘴,彼此之間沒少互相吵架生氣。
可惜這生氣的方式,總是鬧得急了就從動手演變成香//豔畫面,也難怪千載之功,毀于一旦了。
最後琉璃蟬的記錄結束之時,賀離恨卻沒有第一時間立即将意識收回。
他的五感有一瞬間的消失,眼前晃過一陣沉濃的黑暗,而後耳畔響起一道很像自己的聲音,說得是:“你真不覺得自己在拖累她嗎?”
當這聲音響起時,賀離恨原本稍微繃緊的手也逐漸松下來。他閉目又睜:“你們覺得這是個機會?”
他的右眼已經從半黑半紅,演變成了烈焰般的赤色。
“難道不是嗎?”那個聲音說,“別裝模作樣了,天魔對你的臣服從來都有目的,你不早就明白這一點了麽,忘掉你自己吧,投入到我們的懷抱中來,就能擺脫一切愧疚自責的痛苦,自由自在……”
他的聲音仿佛能消除所有的負面情緒,能抹除掉一切痛苦,将人的思想引誘過來——不止這一次,從簽訂天魔契約的那一日起,賀離恨就受到過許多次它們的诘問與誘惑。
重現當年舊事的方式,确實讓賀離恨心神動搖,這種暴露出來的“可乘之機”,足以令這群蟄伏已久的生物怦然心動。
它們的聲音在耳畔不斷堆疊,在心中反複回蕩,好似只要稍微松一松口、稍微産生一點類似于‘想獲得解脫’的心思,就會被徹底吸入進它們的群體當中。
就在此刻,賀離恨輕輕動了一下手指,那條素來躺在刀鞘裏犯困偷懶的魔蛇從袖口中伸出來,它眼眸猩紅,渾身湧動着漩渦般的、吞噬一切的氣息,它爬到賀離恨的肩膀上,沖着那道聲音的來處張開嘴巴。
嘶——
蛇信一顫,灌入腦海的無形吼聲從血盆大口中傳出,這條平日裏只有筷子長的黑色小蛇瞬息之間化為一條巨蟒,長長的蛇身将賀離恨環繞起來,獠牙尖銳,上面閃爍着幽紫色的毒光。
就在魔蛇向天魔的方向咬去時,所有的引誘聲、揣測聲、引入堕落聲,都被魔蛇的大口吸入,連一絲一毫響動也聽不到。巨蟒翻身沖去,毒牙追逐着黑暗當中最濃郁無形的那片陰暗。
此事發生在電光石火之間,連一個呼吸也沒有走過。賀離恨盤坐在黑暗當中,手指緩慢地敲着自己的膝頭,眼中的猩紅如潮水般褪去。
當初梅問情注意到他的眼睛時,他便回答,此事無礙。賀離恨當時還有半句沒說:如果想要找死,那就殺掉。
要知道,簽訂契約的是雙方,能夠毀約吞沒對方的,也不止狡詐的魔。
因為契約的緣故,賀離恨的心頭響起一聲尖銳的叫聲,衆天魔的哀嚎此起彼伏,那些暗域生物比誰的底線都低,立刻轉性求饒。
“尊主饒命,尊主饒命,是它們逼我幹的啊。”
“尊主,都是那個領頭的飛天魔,我們可對您忠心耿耿吶!”
“這蛇什麽時候這麽……啊!我這就吃了你這個蠱惑我們反抗尊主的叛徒!”
不等賀離恨開口,湧動的暗域之間,似乎已經翻臉扭打成一團,以示效忠。而那頭漆黑的巨蟒而居高臨下地盤踞着,蛇信甩動,獠牙邊正有點點紫光消散,正是吞掉天魔元神的跡象。
賀離恨是沒有那種好心留給它們下次機會的,但正在此時,一道清越如溪水的聲音突破了黑暗,薄薄的金光從面前映起。
“賀郎君手下留情。”
金光驅散天魔幻境,露出原本安靜禪房的模樣。瀾空禪師手持佛珠,整個禪房靜室都被一種剔透的金光環繞,似乎早就預備好叫醒他的。
瀾空道:“小僧的師尊為此事惦念許久,生怕郎君出了差錯,牽連着道祖大人。沒想到賀郎君的心思提防,不亞于這群天魔。”
賀離恨:“這話聽起來不像是誇我,禪師,我跟梅問情待得久了,對別人話裏的意思敏感得很。”
瀾空道:“道祖逍遙慣了,我等佛修卻謹慎清修,言語動念之間皆有分寸,郎君多心了。”
他邊說還邊點點頭,清俊的臉龐上流露出些許純良的意味。
兩人說話之間,這道剔透的金光已經照在賀離恨的身上。天魔幻境結束,魔神也失去了追蹤它們吞入腹中的機會,正化為筷子長的小蛇,盤在賀離恨的指間磨蹭撒嬌。
不等這些魔物松一口氣,金光便穿過賀離恨的表面,映出他身後整整一面牆那麽多的虛無紅咒,血紅的契約咒文鋪展而開,上面湧動浮現出一頭又一頭的天魔蹤跡,它們或是美豔、嬌柔,或是狡詐虛僞,或是滿口甜蜜謊言、誘人心神,有外表如人,美麗至極的,也有三頭六臂青面獠牙、面目扭曲之魔。
這些天魔品種不一,皆生存在暗域當中,它們的面貌在咒文中浮現出時,同樣的慘叫也在契約之上形成文字,整個半空飄動的咒文都在顫抖。
然而通透的佛光照入咒文時,這種劇烈顫抖頓時止住。
瀾空禪師垂眸低頭,口中誦念經文,他手中每一個印着符號和佛語的珠子,都在波動之間溢出一層一層的教誨聖言,無數洗滌人心的經文之聲灌注進去——
嘩啦!
血紅契約猛然不動,上面的天魔吼叫和嘶喊慢慢安靜下來,原本緊閉的門戶被術法施展時驚起的風吹開,猛地撞在一側,響起重重的吱呀聲。
門窗吱呀,咒文裏的天魔也昏昏沉沉、渾渾噩噩,被瀾空一手佛印,封進了刀鞘當中。
賀離恨詫異地看了他一眼:“你怎麽知道這刀鞘……”
瀾空頓了頓,回複:“師尊早就囑咐小僧,要為郎君解決此事,而郎君進門時,小僧便見到鞘上的紋路不凡,有改造過的跡象……方才郎君閱讀萬劫書時,我便想起道祖大人無所不通,便私自試了試,果然如此。”
“禪師真是體察入微。”賀離恨真心實意道,“你們生死禪院的心法運轉起來,也是讓人大開眼界。”
瀾空道:“不過是模仿師尊的樣子,教誨一些身在苦海、執迷不悟的生靈罷了。”
賀離恨還要再誇,被這句話噎住了,将滿腹的誇贊之語塞回去,心想:我剛要說你這功法霸道恐怖、侵奪元神,比某些魔功還要強橫詭異,你就跟我說得如此光明正大、一股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意思……可你們生死禪院的出家人,看起來也不是很像正派嘛。
慧則言菩薩确實不是修真界衆人眼中的“正派人士”,她雖然心系天下,但行事作為自有半步金仙自己的理由,而不是喊着“匡扶天下”“替天行道”的口號,就能标榜正派的。
瀾空似乎看出了賀離恨在想什麽,他繞過小案,當着賀郎君的面伸手檢查了一下刀鞘,确認原本空餘之地魔光湧動,不僅全都活着,還封印得十分良好,忽然問:“道祖可像是正道人士麽?”
“她當然……”賀離恨想說她當然好,然而脫口而出三個字,卻發覺對方問得不是好不好,聲音微頓,嘆了口氣,“她那人,怎麽樣也都得忍了,難道還有人能改變她麽?”
能夠改變梅問情的人,這不就在眼前。
瀾空看破不說破,将刀鞘交還給他:“幸不辱命。郎君可以不再擔憂天魔侵擾,但依舊能操縱控制,如臂指使,這柄設計高明的魔鞘,看上去也完整了不少。”
賀離恨接過,視線卻穿過瀾空的肩膀,忍不住看了看那方小案上的《萬劫書》和《因果箋》,心中對那剩餘的、沒有講完之語,還是頗多留戀與期待。
瀾空通曉人意,只一個眼神便心領神會。他轉身過去,将兩物拿起,一并交給了賀郎君:“此物本就是師尊煉制出來,為了解開郎君與道祖之困境的,如若有所幫助,自當送歸琉璃蟬的主人。”
能夠留下這些東西,得益于當年慧則言菩薩在梅問情的準許之下,在賀離恨的神魂之中留下了一個琉璃蟬的标記,無論乾坤颠倒、時光轉回多少次,他的元神不變,琉璃蟬也就一直隐遁在無形之中,跟随記錄。
當初的道祖大人和慧則言菩薩,可是在三十三重天上耗費心血、做過諸多嘗試的,其中還得益于琉璃蟬的記錄,才能發現兩人偶爾疏忽的地方。
賀離恨接過書和因果箋,收入儲物法器之中,向瀾空道謝。此事完畢,賀離恨也打算擇日再繼續看完,兩人便一同準備去尋找道祖和菩薩。
方才那淨化的陣仗太大,門又被疾風震開。賀離恨一轉過頭,便見到門外不遠處,梅問情正将一道絲綢化為拂塵,指尖慢悠悠地轉着拂塵柄,見他望過來便笑。
他只在這禪房待了不過半日,然而卻恍惚間經歷過兩輩子一般,此刻見她,不免思緒湧起,心情激動,轉眼将瀾空禪師忘在腦後,跑出去一把撲進她懷裏,半點資深修士的分寸和穩重都沒有。
梅問情接了個滿懷,險些又讓他撲倒。她的手臂環住對方腰身摟緊,好懸才穩住,額角讓他碰了一下。
梅問情假裝被撞疼了:“哎呀。”
賀離恨勾着她的脖頸,見自己莽撞了,便伸手摸了摸,又湊過去吹吹,說:“撞到你了?我好久沒見到你了。我有好多話要……”
話沒說完,梅問情身側右後方,存在感低到仿佛隐形的慧則言重重地咳嗽了幾聲。
賀離恨一骨碌從她身上下來,耳朵紅得要命,卻還板起臉,這張臉別的不說,扮起嚴峻冷酷來總是好用。
梅問情笑得不行,握着他的手:“好久沒見我?也就一盞茶、一局棋的功夫。”
賀離恨甩開她的手,壓低聲線:“菩薩在你怎麽不提醒……”
“我也不知道賀郎這麽想我。”梅問情追過去又牽住他,眨了眨眼,“她雖是出家人,也是半步金仙,世間種種,她什麽沒看過?”
說罷,又将郎君拉近些,與他竊竊私語:“反正我們要回人間了,只不過在成親之前,還得抓一個人。”
賀離恨立刻警覺:“什麽人?”
梅問情道:“一個年輕男子,是從……”
她剛說出前半句,賀郎君的視線就從警覺變得難以置信,透出一股虎視眈眈的味道,他磨了磨後槽牙,聲音更低微,但咬字格外清楚:“成親前你還要找個通房?你可想清楚了,我肚子裏還有——”
人間的規矩他不知道,但裴家的規矩,賀離恨卻一直都清楚,那些同母異父的嫡姐、庶姐,哪一個不是成親前,就借着知曉人事為由,收了一屋子通房小侍?
“……”梅問情一時都沒反應過來,愣了一下,道,“通房是教閨房敦倫的,你和我,還用教?”
兩人說話聲音低微,停在房門口的瀾空禪師也沒有窺人隐私的愛好,只是遠遠看着賀郎君跟道祖親密交談,正心情愉悅時,雙眼忽然被一只手捂住。
瀾空:“……師……尊?”
慧則言菩薩沉默須臾,殷切囑咐:“你還年少,這種場面你把持不住,眼不見為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