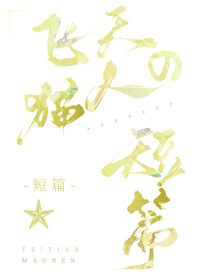落棋無悔
百曉閣。
今日是家宴。
許鹿竹和州南栀坐在椅子上,桌面上放滿了茶水點心。
廚房裏,京墨和劉裴玄正忙着煮菜,閣主将所有下人都給打發走,只剩下兩個男人在廚房裏忙活。
“南栀,帶裴玄來,是有什麽好事宣布嗎?”
閣主那麽提問,許鹿竹也很好奇的看向州南栀。
要屬最好奇的便是州爺爺了,她多日不見州南栀,對于她的婚姻大事,始終是心頭上的一股疙瘩,雖說他如今做不得楠嘉郡主的婚姻大事,但希望她這個照顧了十幾年的孫女一輩子幸福是他的唯一願望。
州南栀一向淡定,她既然帶了劉裴玄過來,便知道會被那麽詢問,“沒有什麽好事要宣布,只是想着京墨一個人在廚房忙活,作為一同成長的玩伴,實在是不忍心,索性叫一個人過來幫忙。”
幫忙,随便叫了一個人過來幫忙,想着,閣主的嘴忍不住抽動,擡了擡眼皮。
州爺爺盯着門外,那劉裴玄的模樣還在他腦海中回蕩,長相身材氣質并不查,和陳緣對比,兩種不同的人,但這小子又多了一份執拗和不甘,“我聽鹿竹說,這小子喜歡你?”
許鹿竹好心提醒了一句,“州爺爺,他是劉少卿。”
“對對對,是劉少卿,那這劉少卿和我們家南栀是不是很相配。”
州南栀撂下茶盞,将爺爺心中的火苗一股澆滅,“州爺爺,劉少卿家裏面自會給她說親的。”
聞言,州爺爺只輕嘆一聲,“你何時才能安定下來呀。”
許鹿竹叉開話題,“父親,這阮家最近在京城風頭過盛,他們這種大家族不會不知道要低調,如今這一出她們是要唱什麽戲嘛?”
閣主嗯了聲,“有些也不是他們傳的。”
許鹿竹不敢細問,只單單點了點頭。
這邊越是安靜,廚房便越是吵鬧。
京墨看向美其名曰來幫忙的劉某人,深深的嘆了口氣,這不是州南栀的報複。
往下一看,這個已經洗了兩遍的菜,還有些黃葉在上面。
“劉少卿,您真的是來幫忙的,您就說你會些什麽?”
劉裴玄仔細想了想,“我會監督。”
京墨:“……”
“劉少卿,那你看看飯煮好了沒有吧!”
劉裴玄攏了攏衣袖,優雅的走姿朝着那邊前行,“今天天氣炎熱,要不然我們改為喝粥。”
京墨翻着鍋裏面對魚,順着他的話語望了窗外一眼,秋葉落下,滿院子都是。
實在是無語的看了他一眼。
忽而又覺得有些不對勁。将魚給盛了出來,快步走到他身邊,“飯變成了粥,劉少卿,不是讓你煮飯嗎?”
他瞅一瞅那粥,再看看京墨,“喝粥對身體更好。”
嘴硬,京墨握緊了手中的湯柄,忽而掄起,朝着她擊去。
劉裴玄往後閃躲,“總該收斂些自己的脾氣秉性。
京墨将湯勺往左一抛,轉身離去,“我教你。”
一個時辰過後,五人坐在餐桌前,也算是滿漢全席,閣主握緊手中的筷子,望了望桌面。
實在是不知道該動那一盤菜。
他閉了閉眼睛,夾起一根青菜,放進嘴裏淺嘗,認真咀嚼兩口之後。“你這青菜怎麽一股雞蛋味。”忽而,頓聲,伸手從嘴裏面拿出了一粒蛋殼。
兩個廚師低下頭默不作聲。
許鹿竹笑着打圓場,“要不您嘗一嘗其他菜。”
他向來聽許鹿竹的話語,“這排骨,怎麽那麽淡。”
“這雞肉,怎麽那麽紅,加了什麽特殊食材。”他特意看了眼許鹿竹,期待她說出這是什麽補身體的中藥。
“這是雞血,應該是沒有煮熟,閣主,州爺爺,您嘗一下這道魚。”劉裴玄将那碗魚肉移到他們的面前,這碗魚肉是他全權操作的。
州爺爺剛剛将筷子放下,州南栀給他杯中添滿了酒,“劉少卿是第一次下廚,有些錯誤還是可以原諒的。”
聽他說完,閣主和州爺爺對視一眼,又默默拿起了筷子,将劉裴玄做的菜都給淺嘗了一遍。
将這些東西吃完,他看向許鹿竹,語氣委婉又明史,“鹿竹,你上次給我準備的蓮子羹,好久沒有嘗了。”
“好,父親,我也正打算煮一些,作為飯後甜點的。”
“靜和公主和躍遠将軍的婚禮舉辦之後,也該給你們準備了,都拖了那麽久,你就不怕鹿竹被別人拐走。”
京墨很有底氣回答,“不會。”
閣主微眯雙眼,“鹿竹,我這有一些青年才俊的世家公子,你要不要了解一下呀?”
京墨看着自家這個老不正經的父親,每次積累的僅存的父愛都會被她作得煙消雲散。
許鹿竹眼神看了他兩眼,“父親,那我們有空了就開始選一個黃道吉日。”
飯後,京墨被支開。
閣主特意留下了州南栀和劉裴玄,京墨和許鹿竹在廚房洗碗,他忍不住說道,“在他心中,你和州南栀是親生女兒,我就是女婿,如今他看劉裴玄也和看我一樣了。”
許鹿竹将碗放好,“我忽而不确定,不确定南栀是如何想的。”
“她喜歡劉裴玄,比當初的陳緣更喜歡。”
許鹿竹沉默了一會兒,又緩緩道來,真誠熱烈,“她喜歡劉裴玄,但她更喜歡自由,她想出去,不會一直待在京城。”
“她同你說過?”
許鹿竹秒回,将其隐瞞了下來,“并未,但我想,我們成親之後,她就要離開了。”
因為足夠了解,因為許鹿竹懂她,所以知道她會離開。
許鹿竹察覺自己說得多了些,坐在椅子上,雙手搭在膝蓋上,岔開了話題,“剛才我問父親的那個問題,阮家如此,是官家容許的嘛?”
京墨忙看向外面,環顧四周,确定了沒人,“京城之中,從未有過最為安全的地方。”他上前兩步,蹲在她的面前,“正所謂捧得越高,摔得越慘。”
許鹿竹低下頭,這一刻,她知道了,也有所猜疑了。
阮家聲名大噪,皇上是有所忌憚的,皇上在打壓,所以他們想躲,也躲不了官家的手掌心,這京城都在官家手掌之下。
“阮家縱然有何錯,是因為豫王勢力太大,與靖王不平衡嗎?”
京墨伸手扣住她的後脖頸,“官家心中有數,至于下一任皇帝,官家自會定奪,鹿竹,不論如何,百曉閣都會是你的後盾。”
她擡下眼眸,皇家貴族的事情自然輪不到自己,可這情形,明顯就是很熟悉,熟悉到許鹿竹有些害怕。
前廳。
閣主剛剛詢問完劉裴玄的家室,他更是一一告知,百曉閣縱覽天下消息,這點并瞞不過他。
“南栀,州家,百曉閣會替你守好,不論你奔往何處,百曉閣都會是你的後盾。”
這是百曉閣閣主說的最後一句話,劉裴玄站在院中許久,這句話在他腦海中回蕩了千遍萬遍。
他伸手朝後擺了擺,不一會兒,一張椅子就在身後,他順勢坐下,手扶着太陽穴。
州南栀不會久留在京城之中,他早就知道的,可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騙自己,希望她能為了自己留在京城之中。
他不是不喜歡周游世界,恰恰相反,他小的時候就随二叔常常出使個州各國,外面是美好的,但也是兇險的。
劉家,下一任絕不是他當家做主,在劉家,他也算是自由的。
今日日歷,宜婚嫁。
李家。
李躍遠乃家中獨子,姐妹衆多,不出意外,以後李家自是要交到他的手中,李家向來以家和萬事興為主,老夫人在時便不允許分家,如今李家一大親戚都在夾道歡迎他的到來。
李躍遠勝仗歸來,又即将迎娶公主,李家人更是上了一層樓,二房三房的叔叔嬸嬸更是因為他仕途又上了一步。
京城之中敲鑼打鼓。
宮殿之內,靜和公主剛剛梳妝打扮好,“過了今日,也就為人妻了,公主,老奴住您幸福美滿。”身邊從小伺候她長大的嬷嬷又叮囑道,“公主,老奴也多嘴一句,你嫁入将軍府之後,平日裏也多收收脾氣,李家有四房,在宅子生活,總歸有些玲珑心,你要多注意些。”
“嬷嬷,我知道,再說了,有嬷嬷您和素心在,我不會受人欺負的。”
嬷嬷從小看着她長大,已然是将她當做親女兒看待,衆多人中,她除了聽父親的話,也就只有嬷嬷能說自己的錯誤。
外面炮仗聲響起,是驸馬前來接親了。
許鹿竹和州南栀守在門外,就等着好好宰躍遠将軍一頓。
劉裴玄看着穿着大紅袍的新郎,手摸了摸下巴,“躍遠将軍有好些珍藏了十幾年的酒。”
京墨眼神一挑,“還有些私人訂制的武器,也送給鹿竹防身一下。”
劉裴玄啧嘆兩聲,“論說武功,我們嗆的慌,從文入手吧!”
“難不成對詩,這些文鄒鄒的東西,算了。”
“猜謎語。”
“猜燈謎。”
兩人還在商讨,州南栀幽幽來了一句,“你們不是新郎官那邊的嘛?”
兩人對視一眼,這才了然為了對付許鹿竹和州南栀,躍遠将軍讓兩人提前來這等着,但兩人哪裏敢,詢問幾句便被州南栀不痛不癢的怼了回去。
“鹿竹,你該不會讓躍遠将軍猜謎語吧!”他覺得兩人心有靈犀,定會往一處想去。”
許鹿竹搖搖頭,“不會那麽簡單。”
還在商讨之中,躍遠将軍一行人便來到了,新郎英姿飒爽跳下馬去,大步超上前來,朝着京墨和劉裴玄挑眉,兩人便來到他身邊。
“躍遠将軍武藝高強,聽聞劍術了得,我指幾個地方,您将銀針攝入,對的地方便同意你将靜和公主接走。”
躍遠眉峰一挑,看到州南栀手中那些細細的銀針,那是給病人針灸的銀針。
他看向京墨和劉裴玄,“要不兄弟倆,你們看看誰能為了弟兄的婚姻大事犧牲一下?”
兩人對視一眼,皆轉開頭,劉裴玄又看向雄安,“你們是一起長大的弟兄,想必配合默契。”
“她們倆是你們最重要的人,肯定互相了解。”雄安怼了回去。
“這是還沒有開始,新郎就起內讧。”州南栀嘲笑道。
此話一出,幾人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不僅沒有邁出那一步,相反而言,還往後退一步。”
州南栀和許鹿竹互相看一眼,“那便各退一步,讓兩人一塊上吧。”
這個主意讓兩人沉默,擡頭看天空,不讓眼角的淚水落下。
躍遠咳嗽一聲,“那便開始吧!不如我做靶子,讓我弟兄們投箭。”
此法一出,衆人眼角的悲傷即刻散去,接着而來是争先恐後的要求出戰。
躍遠雙眼微眯,看着這幫變臉迅速的孫子。
新郎官當靶子,客人圍成一圈,穿到宮殿裏的公主坐不住了,她掀起蓋頭,“欺負本宮的驸馬,簡直是太過分了。”
“公主,這蓋頭不能自己掀,應該讓驸馬來。”嬷嬷着急喊道,素心又趕忙給她将蓋頭放下來。
外面紛紛安靜下來,看着新郎官頭上頂着的蘋果,肩膀兩邊放着小小的栗子。
随着銀針射去,站在州南栀旁邊的劉裴玄一橫,将州南栀隔在身後,穩穩當當的接過那從暗處而來是箭。
頃刻間,場面亂做一團,京墨快步閃到許鹿竹身邊,順勢拉過她的手,護在身後。
“不好,有刺客。”
外面聲響過大,傳進了室內,靜和不安詢問,“嬷嬷,外面是如何了?為何如此吵鬧?”
素心看了眼嬷嬷,在公主耳旁叮囑,“公主,我去看看,您待在這,不要出去。”
忽而黑衣人起,公主府外,皇上親賜的宅院。
黑衣人似是有目标而來,朝着公主府內,躍遠将頭上的蘋果,肩兩旁的栗子拿下,朝着在前鋒的黑衣人射去,蘋果擊打黑衣人的頭,兩顆栗子将他手中的劍給擊打而去,黑衣人視賓客置之不理,今日目标明确。
京墨和州南栀,劉裴玄幾人即刻意識到,護住那宮殿,不讓黑衣人接近。
躍遠将軍跟随着許鹿竹進入,殿內,靜和公主披着蓋頭,躍遠将軍上前,将她護在眼前。
殿外,一團白燕似起。
白煙起,夾着絲絲五石散的味道,許鹿竹躲避着黑衣人的進攻,拉住京墨,在他耳旁悄悄說了一句話。
他即刻捂着唇角離去。
“地上有蠱蟲。”州南栀提醒着,鞭子朝着地上甩去,那白煙遮擋住了蠱蟲。
白煙越來越多,衆人已然是招教不住,門被攻破,劉裴玄接過州南栀甩來的劍,朝着黑衣人襲去,大婚之日見血不吉利,幾人也只是将黑衣人趕走,不曾想着下死手。
蠱蟲密密麻麻襲來,各種顏色交疊,如地獄伸出的魔手,朝着那些目标人物襲去。
更是爬進了公主殿內,躍遠将那些蠱蟲踢開,不讓其近身。
蠱蟲席卷,衆多士兵沖進,火把退卻一部分,接着而來,是水潑墨如畫,散去一部分蠱蟲,然水澆滅了火,那些被火席卷的蠱蟲得以逃生。
一一跟着溜進殿內。
“蠱蟲,黑衣人,哪一樣不是沖着公主而去。你也需保護好自己。”劉裴玄趕到州南栀身邊。
草藥如大雨紛紛落下,那些蠱蟲随即散去,水将煙霧給散去。
蠱蟲進去,将宮殿裏的衆人匆匆趕出,一抹紅衣抱着一襲綠衣,将黑衣人視線全都吸引過去了。
賓客幾乎散去,許鹿竹餘光瞥見角落裏的芳沁公主,正匆匆忙忙遠離而去。
她轉過頭,身子被推開而釀嗆了一下,就見京墨擡腿将那黑衣人一腳給踢開。
眼見黑衣人都圍向躍遠将軍和靜和公主幾人。
州南栀起身,不一會兒,落在躍遠将軍身後,劍如疾風,朝着靜和公主而去。
一抹銀色從眼前閃過,州南栀手中的鞭子正想揚起,“州侍衛。”
一聲呼喊,白煙再次襲來,鮮血霎時間賤出,手臂上忍痛感襲去,穿進心裏面,州南栀咬牙,回頭未看見人影。
卻見許鹿竹追過去的身影,那黑衣人攔住許鹿竹,身後襲來的黑衣人與那躍遠将軍撕打起來,靜和公主想掀下蓋頭,被躍遠将軍攔住。
偷襲的劍朝着兩人奔了過來,許鹿竹推開靜和公主,然黑衣人攔住她,她手一橫誓要護住自己,那劍橫刺過額頭,血濺落在京墨身上。
只差一點,就差一點,官兵的救援晚了。
州南栀被推擋了靜和公主一下因而手臂受傷,許鹿竹額頭被劃傷。
黑衣人抓住了,身上沒有刺青,那些蠱蟲和帶着五石散味的白煙卻讓官家怒震,竟然膽子大到要鬧自己女兒的婚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