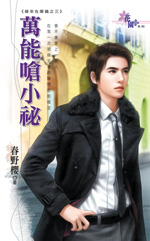往事歸故裏
許桓望着這從小一同長大的人,情誼早已經化為了深厚的血緣關系。
長嘆一聲,無奈又氣,“你是我肚子裏的蛔蟲嘛?我是不是什麽時候放個屁,你都知曉。”
十幾年未見,兩人的情誼也從未散去,宛如從小到大般鬥嘴。
“你要逃去哪?你孫女阿竹呢?怎麽辦?她嫁人之後呢?帶着她丈夫孩子一塊逃?就怕她的身份暴露了,她相公若是嫌棄甚至害怕又當如何?”
“是,啊竹也可以不嫁人,但她還年輕,難道要東躲西藏一輩子?還有小栀子,當年老州去世時,州将軍在外征戰,托付我們照顧小栀子,難不成,兩個女孩子的命運就是躲藏一輩子?”
許桓沉默了一會,才又呢喃說道,“可至少她們活着。”
陳益幹裂的嘴唇微微張開,卻吐不出一句話。
“那你呢?從前是辰王的老師,如今在朝中又跟了哪位皇子?”
“靖王殿下,眼下官家身體抱恙,靖王和豫王兩虎相争。”
“宋居誓死為辰王效忠,如今你跟了豫王,我可沒有什麽遠大志向,什麽建功立業,如今這生活挺好。”
陳益漠然,這便是另一個來找他的目的,如今三兩句話便被他看透了,更是給拒絕了。
他是一無所有,可依着他的謀略,是一位上等的謀士,自己于他而言,不過是班門弄斧。
“十二年前的事情影響太過,折損了不少人,你許家真不想平冤?歷史永恒流傳,背太久的罵名你許家祖宗當真願意?”
許老冷哼一聲,“冤情,你這是不服官家的決斷。”話裏帶着暗暗的怒氣。
“你…”陳益随後長嘆一聲,惹自己生氣是許桓的拿手絕活。
“我如今是半截身子要入土的人了,拿什麽去平冤”
“阿竹呢?還有小栀子,怎麽,你瞧不起她們。”
正是因為是自己唯一的孫女,他更不希望一輩子為了報仇而活,他只希望,許鹿竹能平平安安,幸福的度過此生,這或許也是她父母親的願望。
“實在不行,京墨,這小子我看不是一介草夫,許老,你收養了一個大人物。”
許老眼神堅定,“他死了。”
陳益還想要再說些什麽,然而被他打斷了。
“你不必從他那下手,京墨和許家如今是一點關系都沒有了,京墨是不會讓阿竹和小栀子去參和這件事的,所以,京墨的決定也是我的決定。”
“為什麽你知道,京墨知道,卻唯獨隐瞞她們兩個人?”
許桓沉默沒有回答。
兩人往下慢慢走,來到了一處河水旁邊,水嘩啦啦往下流,将陳益髒兮兮的臉頰給描繪一清二楚,他雙手捧着水擦了擦臉頰,又喝了一口來自這山間的甘甜清水,水滴順着手指滴落,蕩起一圈又一圈光波。
陳益還是不死心,回去時,人多眼雜,也不方便去找他,這最後的機會他不得不抓住,“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,但你先保證不跳河自殺。”
正蹲在一旁洗手的許桓擡眼望向他,“但我不能保證你不跳河自殺。”
陳益饒好的溫文爾雅的面孔此時臉色鐵黑,咬牙切齒,“你這死老頭子。”
罵了他一句解氣之後,臉色緩和下來,但卻像是緩和過了頭,變得更嚴肅認真了,“我與兩個小女孩都見過面,感覺她們并非什麽都不懂,我又去和小栀子的師父聊天,她好像在準備離開衙門的事情,要入大理寺。”
要入大理寺。
要入大理寺。
這句話一直環繞在許桓耳畔,他腳步走得飛快,但那句話無論如何像是甩不開般,緊緊跟随着他。
與此同時,去京城的路在他的腦海中回蕩。
陳益知曉他的脾氣,根本就拉不住他,并未有太多擔心,兩人分路前行。
衙門。
知曉了陳大人回來的消息,知州大人便讓她們停止查探,這件事從此以後閉口不提。
在場的除了陳緣、方冷等人表現略微驚訝,其餘人一言不發,只是聽到了一件普通到不能在普通的小事。
州南栀擡起眼眸,“那關于淩赤侍衛的案件,還需要繼續查下去嘛!”
“查,這件案件要繼續查下去,最好在陳大人離開時将其查出來,也讓我們衙門的辦事效率在陳大人眼中能得到重視,說不定以後,能有些賞賜。”
許鹿竹眼神落在州南栀身上,總覺得這個問題不應該是她問出的。
出了衙門之後,許鹿竹再次折返回來,她知道,今日是方冷值夜班。
“鹿竹姐,你怎麽又回來了,你是打算陪我一起值班嘛?”
她提了提手中的食盒,“過來給你送夜宵吃呀,順便幫南栀拿些需要用的東西。”
他笑了兩聲,“鹿竹,你好會說話,這明明是說反了吧!”
她拍了拍她的肩膀,示意他坐下,将食盒裏的菜肴點心,還有甜品一一拿出來,“木臨呢?”
“去查另一個案子了。”
“那留一些夜宵給他。”
他抓起一個雞腿就往嘴裏面啃,這是鹿竹姐獨家釀制的雞腿,是外面買不到的,“鹿竹姐,上次南栀姐就已經将東西全都收拾了,難道是又落下什麽東西了嘛?”
許鹿竹眼中的震驚很快便一閃而過,“嗯,落下了一件東西,正過來幫她取。”看他吃得開心,許鹿竹啓唇,“你若是一個人辦案,沒有了南栀姐的指導,害不害怕。”
他擺擺手,“起初害怕,但南栀給了我她的工作經驗,又鼓勵我,還那麽相信我,我怎麽能讓她擔心,按道理應該是我擔心她才是。”
答案已然呼之欲出,許鹿竹垂下眼眸,如此看來,她也知道了。
“鹿竹姐,我還沒有問你呢,你是不是也要和南栀一塊去京城?”
她笑容淡淡,“我還在和爺爺商量中,結果你先不要告訴我,到時候我自己我說,可能就會是一個驚喜了。”
“嗯,我知道,我懂,當年京墨哥就是教我這樣追女孩的,我,,,。”意識到自己說多了,方冷立即閉嘴,想給自己兩巴掌,小心翼翼看過去,又小聲詢問,“鹿竹姐,我,…..,你沒事吧!”
“我沒事。”她起身,“夜深了,我拿個東西就回家了,你晚上注意安全。”
許家。
許奶奶做好飯菜之後,老頭子躲在房間裏還是不出來,回來時,整個人神情恍惚,無論怎麽詢問他就是不理。
“爺爺還是在房間?”許鹿竹想進去叫爺爺吃飯,被許奶奶給攔下,“算了,不用理他,餓了自己會出來吃,估計是在山上采草藥時累壞了。”
吃飯時,許奶奶給她夾菜,“鹿竹,你臉色那麽差,是不是身體不舒服了。”
她回神,“沒有,是我擔心爺爺。”
“他沒事的,自己也是個大夫,吃個雞腿。”
她晚上吃得不多,剩下半碗米飯便拿去喂雞鴨了。
許鹿竹手中的碗不知擦了多少次,眼神恍惚,腦海中一團亂麻。
她不知南栀要去京城幹什麽,也不知她是不是知道這件事了,更不敢去詢問,一切都撲朔迷離,糾着幾人,在漩渦中心不斷旋轉,找不到方向。
許奶奶推門走進去,許桓拿着兩份庚帖在燭火燈罩下看了一遍又一遍。
十幾年過去,他的眼神還是沒有半分蒼老,可躲藏讓他的背弓得越來越彎。
“餓不餓?”她站在前面,燈光下倒映着她的身影,也是一樣的彎,頭低得也更低了。
許桓沒有回答,一雙渾濁的眼神仍舊離開了那兩張庚帖,語氣僵硬,“你說是這庚帖上的名字好聽還是我給她們起的名字好聽?”
許老太沒有回答,将庚帖收了起來,“十二年過去了,你猶豫了?”
“我今天和陳益見面了。”
許奶奶眼神中的震驚很快一閃而過,轉而是疑惑,揣着答案詢問,“勸你回去?還是勸我們遠走高飛。”
“回去是不是送死?”
“死?我們本來就是背着把刀生活,無論什麽決定,我都無所謂了。”
“那鹿竹呢?”
她緩緩轉頭,狠下心來,“你當初把京墨趕走,我應該阻攔的,若是他一直在鹿竹身邊,我倒是放心,老頭子,我現在相信兒孫自有兒孫福了。”
“京墨在京城,你同意鹿竹去京城嘛?”
許奶奶沒有搭理他,良久,埋怨了一句,“我的決定你何時聽過。”